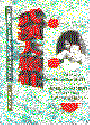
武漢大旅社
白色恐怖下最曲折離奇冤獄案
黃秀華 著
出版社:台北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年1月初版第一刷
黃秀華 簡介
台灣輔仁大學物理系
美國 Marquette University 物理研究所
曾任美國空軍基地 Computer Scientist
現任 Electronic Data System Corporation 系統工程師
長期在海外從事台灣民主獨立運動。 1992年2月在美國洛杉磯組織
「台灣外省子弟台灣獨立支援會」,四月在行政院前靜坐抗議,要
求廢除「刑法一百條」及釋放政治犯而遭逮捕,同年八月和戴鑑、
張忠棟、廖中山、陳師孟等共組「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
惡夜沉冤追憶錄
取自【武漢大旅社】自序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在海內外各報發表一篇《白色恐怖是外省人的
二二八》,文中提及蔣氏父子政權下的白色恐怖,許多外省無辜受難者悲慘的命
運和二二八受難家屬相同,也藉此文在敏感的政治事件紀念日裡,呼籲國人以愛
心與和平非暴力的手段互相容忍,共同為台灣的未來努力。一向不肯刊登我的文
章的聯合報系,也派記者來洛杉磯詢問此文是否由他們獨家發稿。「二二八」受
難者經過海內外人士的努力奔波,已獲得平反;而白色恐怖中的受難者以大陸籍
人士為主,在一個陌生的島嶼上,面對一群陌生的人民和陌生的語言,文化,真
是無語問蒼天,冤情何處訴?
此文登出不久,《國際日報》記者劉玲女士來電,她以一種低沈而感性的聲
調說:「黃秀華,我一直知道妳是誰,很早以前北美協調處的人就查出妳的背景
了。不過,這幾年來妳絕口不提,我就不好追問。黃秀華!妳真不簡單。」命運
使然,簡單人物也得扛起不簡單的任務。接著她說:「妳應該把工作辭掉,好好
花一年的時間把武漢大旅社冤案的故事詳細、完整地記載下來,公諸於世。」我
保持沈默,沒有接腔。對我而言,這是一項沈重、悲痛的任務。
幾天後,聯合報系的《世界日報》駐洛杉磯記者劉永毅先生訪問我,希望就
武漢大旅社冤案做一則呼籲平反式的報導。
美國洛杉磯的台灣人活動中,有三名常露面的外省子弟,即上述《國際日報
》劉玲女士、《世界日報》劉永毅先生和我。我們的年紀相差近十歲,這幾年來
,我們都相當努力去彌補國民黨政權製造出來的族群隔閡,共同推動族群融合的
理念。劉玲和劉永毅也是幾十年來少數在某種機緣中得知武漢大旅社冤案,鍥而
不捨努力揭發真相的記者之一。一九七七年,《大華晚報》的年輕記者李敏欽訪
問我們,準備做一系列詳盡的報導,才報導了兩天,就被官方施壓腰斬,李敏欽
被調查局約談數天,從此不了了之。李敏欽因此成了我家的友人,我出國時,他
也特地來機場送行。
劉玲積極鼓勵我出書的一番建言,令我陷入幾夜無眠深沈的思慮。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日,趕在一群台獨人士被捕開庭之前,我邀請幾位外省子
弟在洛杉磯成立「台灣外省子弟台灣獨立促進會」。同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和台
灣三十一位人士共組「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我們的動機很單純,當務之急
是把一群陸續由海外闖關回台遭逮捕的台獨人士拯救出來。當時,蔣家忠臣郝柏
村仍當政,這些人生死未卜。另一目標是打破四十年來被國民黨視為禁臠的外省
族群所擁抱的愚忠式的統一思想,我們企圖引發理念性的再思考,我們是否無可
避免地做了龍的傳人而必須要一代一代承續五千年來中國文化的遺毒?我們是不
是一定要接受千年不變的大一統思想?在這大一統的謊言下充斥著宮廷鬥爭,人
命如蟻。難道在世界民主人權的潮流衝擊下,我們仍無法拋棄舊有包袱,開創新
的局面?
在推行運動的過程中,我一直強調:「外省族群和所有舊移民的台灣人應該
有命運共同體的覺醒。」「命運共同體」近年來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名詞,可是對
我的家人和白色恐怖受難者來說,卻是血淋淋的酷刑、噩夢,更是一生都抹滅不
去的傷痕。於是我開始執筆記錄這個和台灣人命運與共的白色恐怖真實故事。
我憶起父母入獄的第三年,也就是我十歲那年的某一天,我和哥哥、姊姊、
弟弟正為一天唯一的一頓餐食與一群陌生的成人做爭食的生死戰,在短短的幾分
鐘內搶到幾口菜,正悶著頭吞食之際,大舅臉色凝重地站在飯廳門口,對我們六
個孩子說:「你們的父親都快被槍斃了,你們還有心吃飯?」哥哥、姊姊立刻放
下碗筷,眼淚撲簌簌地掉下來,而兩個年幼的弟弟仍捨不得丟下他們費了九牛二
虎之力搶到手的食物,直到我們用力把他們抓離飯桌,他們只有嚶嚶哭泣。哭泣
是為了饑餓,而不是父母的生死。他們的生死已經離我們愈來愈遠,而無父無母
的我們還得繼續生存下去。在獄中,在獄外,我們一家八口各在兩個不同的無情
世界掙扎……。
一九九五年七月,距離那段悲慘的日子已經三十幾年,我和家人開車由美國
聖地牙哥到墨西哥邊界的城市提瓦納,一群衣著襤褸,滿身污穢的墨西哥小孩尾
隨著我們,向我們要錢。我的小弟左手拿著一根他兒子咬了一口不想再吃的玉蜀
黍,右手拿著另外一根,一面吃一面誇這玉蜀黍味道真好,和以前在台灣所吃的
一樣,順便把左手中的那一根遞去給這群墨西哥小孩,其中一個小女孩搶到,緊
握著玉蜀黍轉身飛快跑去,然後躲在遠遠的角落蹲著吃,其他小孩盯著小弟另一
隻手中的玉蜀黍,更不肯離去。老六再也吃不下,把口中的那一根玉蜀黍也拿出
來遞給他們。
隨後老六告訴我,三十幾年前,在台北車站常常有一群同樣穿著破爛,全身
髒兮兮的野孩子,圍著候車的大人要錢,要東西吃。大人口中咬著一串番石榴,
吃了一半,車來了,順手把剩下的遞出,幾雙小手同時伸出來搶,搶到的小孩一
、兩口吞了下去,舌頭仍津津有味地舔著。這群野孩子其中的兩個是我的弟弟老
五和老六。父母被捕時,老六三歲,老五五歲,富裕人家的子女一夕之間成為在
街頭遊蕩的孤兒。有三年的光景,幸運的我和姊姊被善良的外婆帶回眷村撫養,
因此,哥哥和弟弟那段時間內的遭遇,我並不完全知道。編寫這本書時,我想從
他們口中收集一些故事,所得到的答覆卻是:「我不記得了!」「我忘記了!」
我們六個孤兒各自的內心中都有陰暗的一角,三十年來不曾向任何人提及,包括
彼此之間。日久,就刻意地把它忘了。成年以後,雖經過努力的奮鬥,心頭上仍
隱約留有悲慘童年的遺痕。
從我父母的記憶中挖掘資料,更是每每掀起情緒上的驚濤駭浪。說到他們被
關在調查局毒打七十九天,生不如死,而欲以自殺了生的殘酷,說到司法界的腐
敗惡質,常常令今我忍不住摀住雙耳大叫:「好了!不要再講了!今天寫到這裡
為止。」丟下稿件,一個人開車到海邊去透氣。過了幾天心情穩定下來,我才說
:「媽!告訴我那個死要錢、草菅人命的貪官叫什麼名字?」我在此書中記錄他
們的姓名。當今台灣司法院副院長呂有文就是當年參與審理此案的法官之一。
幾十年來,我避免去碰觸那個傷痕。如今,我開始抽絲剝繭地問:「誰是陳
華洲?」並著手研究調查局的資料,分析案情。寫到一半,我告訴父母,那些人
要整肅的對象不是父親,依我的分析,他們要整肅的是和雷震關係密切的陳華洲
教授,其他六個人、武漢大旅社和一具自殺的死屍則是煙幕。父母先是愕然,繼
而想起許多細節,使我更加肯定這種推測。當年,是誰有這麼大的權力能令幾十
名法官、調查局人員、法醫集體偽造這千古冤案?這一部分就留給讀者去推理。
不知有多少個晚上,我一面回想一面記錄,記憶像一隻聞到血腥咻咻而來的
野獸,讓我從童年的惡夢中驚醒,嚇出一身冷汗。白天,我也常常陷入情緒上的
低潮,我鄰座的同事,美國老科學家華納博士,走過來拍拍我的肩頭說:「麗娜
!什麼事讓你看起來這麼悲傷?看看外面金黃的陽光,生命多美麗!」窗外是一
片亮麗的藍天白雲和綠草如茵的大地,在以民主、人權為立國憲章的國度裡,生
命是美麗的,是享受,是尊嚴;但是對不知人權為何物的中國大陸十一億人口,
和前途未卜的台灣兩千萬人來說,生命是掙扎,惶恐,是最原始的生存。
今年元月,康乃爾大學校長邀請李登輝訪美,不瞭解台灣民主奮鬥史的他,
誇讚李登輝締造台灣民主奇蹟;而李登輝登台演講一開口就推崇蔣氏父子對台灣
的貢獻。七月,蔣宋美齡又受到一批美國參議員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碩果僅存者美
譽加身,以酒宴相待。缺乏對歷史的認識,人類是愚蠢的;缺乏歷史真相的記載
,人類是健忘的。
蔣氏父子來台三年後,我出生;蔣介石去世,宋美齡赴美後四年,我也留學
美國。蔣介石時代,我是白色恐怖的受難家屬;蔣經國時代,我不遺餘力參加海
外的反對暴權運動,希望將來有一天,台灣歷史學家提到蔣氏父子的「功績」時
,也提起白色恐怖中的武漢大旅社冤獄案;展示蔣家父子相片時,也同時展示此
書前頁恐怖政權下六個遺孤的相片。
此書完成之日,或許是我們一家兩代八口,從惡夜風暴再堅強出發的一個起
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