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貼時間: 2013-01-17 14:54: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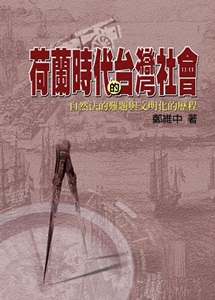 荷蘭時代的台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
荷蘭時代的台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作者:鄭維中
出版社:前衛
出版日期:2004年07月31日
ISBN:9578014449
作者簡介
鄭維中,1974年生,臺灣屏東林邊人。政治大學社會學碩士、荷蘭萊登大學歷史學博士。著有:〈略論荷蘭時代臺灣法制史與社會秩序〉,發表於:《臺灣風物》50卷1期。譯有:播種者出版,韓家寶著,《荷蘭時代臺灣經濟、土地與稅務》。
本書藉由荷蘭時代發生在台灣的幾個事件,來說明荷蘭時代臺灣社會中各族群的互動情況,以及臺灣社會當時的重大變遷。荷蘭人在台經由與原住民締約的程序,來建立政體;並且依照澳門、馬尼拉、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等其他歐洲殖民城市的治理經驗來建立熱蘭遮市(今台南安平)。
作者細緻剖析1637年荷蘭長官帶兵集合南部數村社長老來公審殺人兇手的檔案文獻,提出荷蘭人以領主-領民關係為在台組織政體的原則此一假說。並藉由剖析1639年漢人代表上呈荷蘭政府的一份請願書,來關照當時臺灣漢人市民眼中的東亞世界。
透過作者對第一手文獻的解析,向讀者展現出共居於臺灣的原住民、漢人、荷蘭人三者,不同族群間由於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所交織而構成的豐富社會生活網。本書提供了在殖民國家競爭架構之外,從本地社會生活之學習與創新此一角度來理解臺灣歷史的新視野。
(根據本書原文略述:)
荷蘭在台灣統治38年,將當時歐洲的社會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施行於台灣,成立了一個類似歐洲各地的「等級政体」。
聯合東印度公司成立之法律基礎
(p.5)特許狀(Octrooi),為中世紀君主將所屬主權的一部份授與出去的證明書。東印度聯合公司的成立,基礎就建立在1602年3月20日,荷蘭共和國聯邦議會(Staten-Generaal der Vereenigde Nederlanden )所批准一份特許狀所賦與的法律地位之上。亦即聯邦議會將其執掌國家主權中,所包括的壟斷貿易權,授與聯合東印度公司。當時的發動獨立叛變的荷蘭共和國(低地聯邦)正處於被西班牙帝國軍隊陸地包圍、海上經濟封鎖的艱困處境。於是,各市鎮當政的攝政門閥等級仕紳(Regent),一方面由於領軍參戰,無法參與殖民地經營;另一方面要經濟資源的支持,故將海外區域的準主權,交付給商人,以換取其支持。又以授與貿易壟斷權的方式,提高其獲利。
治理東印度地區的法律架構
(p.13)根據《1602年特許狀》第35條條文規定: ...前述「聯合東印度」公司得在好望角(Cape van bonne Esper-ance)以東,到麥哲倫海峽內之間,以聯邦議會或其主權的名義和君主及實力者(Potentaten)結盟或訂立契約,以建立堡壘及據點(Versekertheden),因地置宜設置長官、軍事人員、司法官員,及其他必要的職位以維持秩序(ordre)、治安(politie)、與司法(justitie),尤其在推展業務。此外,前述長官、軍事人員、司法官員在啟程營業時即對聯邦議會(Staten Generael)或其主權(Overichtheijt)與公司宣誓效忠。
治理台灣的法律架構
(p.20)...為與明帝國發展貿易,總督Jan Pieterszoon Coen與東印度議會發佈《1622年4月9日指令》,任命Cornelis Reijersen為指揮官,率領12艘船聯合艦隊,於15日組成秘書議會,25日組成艦隊議會。6月24日進攻澳門失敗,25日根據艦隊議會決定根據同一分《1622年4月9日指令》的命令採取下一步驟佔領澎湖。之後展開了此一艦隊以澎湖為聯絡處,長達兩年的時間不斷要求與明帝國直接貿易的過程。...當明帝國方面在1623年底態度漸趨強硬後,一方面因為大員一地長久以來為中日走私地點,荷船則藉此與中日商船聯繫;再者整個艦隊薪柴、飲水的運補因地利之便也多來自大員(Tayouan,時指鯤身島),而在澎湖的病員也送到大員來療養,於是在1623年10月25日Reijersen指揮官應Pieter de Carpentier總督之命令,派人到大員來建築城壘。此後,大員即為澎湖議會控制整個聯合艦隊調度網轄下的一個據點。
1624年5月4日巴達維亞的總督和東印度議會決議任命Martinus Sonck為長官(Gouverneur),接替Reijersen指揮官之職務。他在8月3日抵達澎湖,此時,遭逢明帝國海師壓境,故8月18日,聯合艦隊的艦隊議會決議撤退。26日開始拆除澎湖城堡,30日長官發令在大員建城。...大体上,隨著貿易狀況的穩定和大員市鎮的商、漁業發展,與台灣原住民結盟及內陸農業、狩獵開發,越到統治的晚期,議會就越固定於大員(熱蘭遮)城內。此外,隨著基隆、淡水城議會之設置,熱蘭遮議會也漸漸獲得地區性政府的地位。如同巴達維亞中央政府的成立過程一樣,早期的大員長官與議會較具軍事性的機能,晚期則漸漸發展出地區性的立法機能。前述1626年東印度議會的決議中,將大員長官視為東印度議會的當然議員,使東印度議會和大員議會結合起來。總而言之,制度架構的權限劃分在於是議會間的層級關係,而不是地理上的範圍。隨著人員活動範圍與需求的擴張、人際間關係的複雜化,制度架構也因而擴張。
治理台灣本島的封建政体:地方會議
(p.24)直到1635年11月23日長官Hans Putmans 獲得巴達維亞調派的遠征軍(400人)之助,率領600人分為七個連隊討伐麻豆大社後,與西部平原各村落關係才算初步穩定下來。1636年開始舉辦全島各村社首長一同與長官締結封建協約「領邦會議」(Rijktag),之後則分區加開「地方會議」(Landdag)。所謂「地方會議」,即歐洲當時封建政体下「等級會議」的一種型態。
1636年2月舉行首次「地方會議」(Landdag)。20日陸續有28村落的首長(bevelhebbers)聚集到新港村。 21日晚間,Hans Putmans長官,率領一個連隊的士兵登陸新港。雖然已經安排好所有的參加者的就寢處(slaepplaetsen),這些參加者聞訊後還是前來歡迎他。當夜,長官友善的接見這些人,並且,長官還「對他們讚訟和平對他們有多麼可貴,除非必要他不發動戰爭,更不會和居民一樣,為了頭顱而爭鬥。」
22日,開始所簽訂和平協約的確認(bevestinge)典禮。擔任各自村莊發言人的所有長老們(outsten),排成一列,荷方非常冗長、詳盡的向所有的參加者描述將要被確認的「和平」(vreede)的意義:和平有多麼可貴、此後怎樣以合適的方式相互對待,而不是如過去的習慣彼此謀殺。冗長的解釋之後,大致上確定長老們已沒有疑問,再向他們解釋將授與他們的禮袍、權杖、親王旗的意義。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宣誓效忠,確認協約--雙方一起折斷一根稻稈(平埔族人有折草為誓的行為),共同發起誓約,接著典禮開始,由長官號令,長老個別被召喚出列,親身到長官面前,由長官授與袍子、權杖、親王旗。
當目加溜灣、塔卡拉揚、和放索仔村莊的長老受召出列時,他們將檳榔、椰子樹苗親手種植在長官雙腳之前,象徵讓渡主權給荷蘭共和國。授袍的典禮結束後,長官再度鉅細靡遺的向他說明要力圖維繫和平,不止不應反對荷方,而且也不應相互作對。換言之,破壞和平者無疑的會遭到應有的懲罰。
(1636年)2月22日,參加的村落有:新港北方兩天路程的有Tarokei(塔羅凱)、Tirosen(諸羅山)、Dorko(哆囉嘓,內含二村),從一天路程以外山區來的有Tevorang(大武壟)、Taiouwang(台歐灣)、Tusigit(突西技)、大村莊有Mattau(麻豆)、Soulang(蕭壟)、Bakloan(目加溜灣)、Magkinam(馬氣南)、Teopang(大歐龐)、Tivalukang(帝華鹿港)、Tivakang(帝華港);(新港)南方兩天路程的有Takareiang(塔加里揚)、Tapuliang(大木連)、Pandel(萬丹)、Calivong(卡利黃)、Sotanau(蘇塔鬧)、Tourioriot(桃溜溜),在Sotanau南邊一天路程的有大放索仔、小放索仔、Kesangang、Tararahei、Jamich、Sangwang、Flatia(弗拉夏)加上新港共28村。
1644年3月21-3日的北路「地方會議」,60人出席,參加者:首長(領有權杖)、長老(未領有權更但有資格領有者)。列席:議會、政務官(此後為常設)。1644年4月19日的南路「地方會議」(包括東部村落),66人出席。除了1657年因天花肆虐,大多村社首長無法出席,也無法派代表參加,1660、1661兩年因國姓爺攻台傳聞而延期,每年舉行會議。1651年全島聯合315村,66675人口。
從前無古人的放索仔村落的會審,解析 台灣本島領邦法政架構
放索仔位於下淡水河(高屏溪)的南方,(塔加里揚)南方七村,總稱放索,離海岸不遠,人丁眾多。1636年2月,放索村落已和荷蘭人結盟,從未殺害福、客移民、或害荷人。荷蘭人4月時曾派出一名士官駐於此地學習語言,5月到7月,荷人和放索村聯軍跨海征伐金獅島(小琉球),將當地居民收為戰爭奴隸。從結盟到聯軍,放索村的居民對荷蘭人的支援都由一位當地首長Tacomey代表。1637年7月荷蘭教會當局已開始在南方附近各部落設置學校。
1637年10月底,派駐的士官倉促逃歸熱蘭遮城堡,驚慌的向議會報告:Tacomey 已被殺害。根據以往的經驗,這似乎是大規模叛變的前兆。不過此時公司正忙於征伐虎尾壟人,難於措手。虎尾壟戰爭結束後,長官決定傳喚Tacomey的兄弟,探知放索人的真正意向。11月15日後,局勢明朗化,這是一件單純的家族間仇殺,並不涉及其他的村落。於是,23日議會決議,到放索仔村莊去執行這件刑案的審判與處刑,讓原住民暸解到殺害部落首長的後果。11月26日星期四,行動指揮Johannes van der Burch長官登上載滿衣裝整齊、裝備良好荷蘭士兵的三艘戎克船,趁著北風,由熱蘭遮城向福爾摩沙島南方啟航。三艘戎克船上共載有140名荷蘭士兵,由一名尉官Jan Jeurijaenszoon率領。
28日清晨,部隊按照兩個連隊隊形,嚴整的登陸放索社,由受害家族一方的放索人,駕著杉板協助完成登陸。部隊由牧師和尉官率領,嚴整的行進,進駐村莊。兇手方的一半放索人,均已攜家帶眷逃離。當夜扣押一名兇手方的長老Rioulath,他也是5個主犯的唆使者。長官通令五個嫌犯必須自行來接受審判。星期日清晨四時,漢人通事帶來了四位主犯Tarapou,Tipikat,Tamarouwi,Tarubat,第五位因重病無法應訊。
附近村莊Dolatocq(東港),麻里麻崙(萬丹)及搭加里揚的長老們率領共約850人來協助維持審判的秩序。審判就在這些長老們和長官的面前舉行。相關的人士都聚集到這村落。這村落狹長,房舍低矮,有3000人口的大聚落。加上領命前來的外村長老和精壯的外村戰士,使這個村莊的氣氛呈現一股未有的騷動不安。荷蘭士兵既未攻擊,也未燒殺,他村的戰士也同樣按兵不動,使得氣氛詭異又凝重,這個情景就像聯軍出擊小琉球,但沒有攻擊的對象。前幾天,荷蘭人要率軍南來的消息傳回村落時,就引發了恐慌,半數人相信荷蘭人將燒村痛逞,就像虎尾壟和其他地方一樣,於是攜家帶眷連夜潛逃;另一半人半信半疑,但也恐慌不安,於是在岸邊等待荷蘭人的到來。這4位主犯的出現,多半也是在擔憂荷蘭人燒村的恐慌之下,出來投案。
長官、外村長老、本村長老、嫌犯、居民,齊聚在光天化日之上,並且在外村戰士和荷蘭士兵森然羅列的武器金屬光澤之前,開始這一次前無古人的會審。村落插上了奧良耶(Orange)親王的親王旗,長老們則披上黑色禮袍,手持銀標權杖。在牧師與當地預備教師的中介翻譯之下,會審開始了。
謀殺的動機是積年的仇恨。Tarapou是為了報父仇,Tipikat則是為了報姪子的仇。當去年7月爆發天花流行之後,Tacomey一方染病勢力大減,他們便趁此機會報仇,將Tacomey殺死。顯然這是一件單純的仇殺,但是,殺死的對象不單是一位屬民,而是一位長老。因此,其罪惡不止是妨礙了公眾的安寧,而是觸犯了政治上的秩序。長官對此的判決是: 我們對年輕時候發生的問題沒有興趣。因為,若是如此,當初就不應選Tacomey作長老(outste),而應該告發此一事端,由前任長官審理。既然在前任長官主持的選舉中接受他為長老,且誓言加以承認尊敬,作他順服的屬民;何況他又對荷蘭政府誠實忠信,可堪為所有長老的表率。所以,所有參與謀殺的人,都應按照當地的習慣(costume)受相當的懲罰以為鑒戒。
對於根據當地習慣應如何來處置這點,長官則交由參與會審的所有長老來提出。於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所有4村長老們與長官和牧師一起,魚貫進入另一個小屋。他們將在此會商決議對此4人的處罰。
時間似乎凝結了。所有人都在期待事件的終結。按照長官的記載,所有長老的意見都贊成將這些殺人犯判處死刑。因為長老們為了自身的安危,有必要借荷蘭家長對此懲罰以示儆戒,來預防類似事件的發生。為了讓所有的長老個別發紓意見,討論進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長老們和長官達成共識後終於再度魚貫走出小屋。長老們共同宣判了死刑。五個罪犯此時才被捆綁起來,準備受刑。長官下令他們對群眾大聲懺悔自己的犯行,長老們則向群眾宣佈其罪狀,告知每一個人,要繼續效忠他們的長老,而長老則在他們屬民的認可下,矢志效忠荷蘭政府,更因此要以此犯行為鑒戒。長老們的告誡此起彼落,群眾則交頭接耳,一陣騷動後,緊張的時刻來了。
行刑開始了。所有人都對他們無能為力。Rioulat、Tarapouw、Tamerowi在鋒利的軍力下身首分離,驚嘆聲,哀嚎聲,此起彼落...Tipikat、Tarrubat緊接著被帶上刑場。群眾的緊張已轉為莫明的亢奮...此刻,長官卻下令終止行刑!這引發了另一陣譁然和騷動。群眾的情緒再度被挑起了。
長官隨即說明了理由:長官赦免他們,以示「要另一半逃離、叛亂的放索人知道,我們並不對所有人都要報復,而且要他們回來之前,先向長官求和。」並且向那一方的人宣稱,Tacomey長老的兄弟和孩子,已被群眾認可為本村長老,逃離的那一半人,若不和荷蘭政府和解,就不會在他們當中設立長老。
如此,長官不可動搖的最後權威殆無疑義,而長老們對此多少有些訝異。激情過後,亢奮的群眾索取屍體的牙齒、耳朵、頭髮。長官權宜的准許之。
從以上這個案件,可以解析出幾個政体結構上的特徵。
首先,這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與此地原住民結盟之後,首度以執行司法的形式(而不是戰爭的形式),正當的行使暴力。就這一點來說,殺人罪成立的前提,就是戰爭行為的取消。只有在暴力(尤其是生殺大權)為上級支配者所壟斷的時候,其他的任何個別的暴力行為,才會被視為私鬥。從此開始,不只是簽約村落間的爭端不得使用暴力,部內的爭端也不能由暴力解決。
其次,此一案件,並非單純的殺人案件,而是殺害長老的叛亂案件。按照此一判決的理由,突顯出長在法律身份上的特權。殺害長老,不能以一般觸犯公共安寧的私鬥視之,而是一種挑戰合法權威的叛亂行為。此後,長老既經推舉或認可,宣示效忠,就不是一般屬民。
第三點,案件經由諸村長老聯合會審,而不是單獨的視為一村的孤立事件,則是將長老視為超出個別村落公共權力的代表。此後他們不同於一般屬民,代表超村落的利益。而個別長老遭受的問題,他村長老也有解決、干涉的義務,不是由各村社民眾自行解決。
第四點,長官行使了赦免權。這清楚的展現其所具有的完整司法權力。亦即,即使按照法律、習慣來求刑判決,長官也有超越制度的最後決定權。此後,掌握生殺大權的終極決定者,只有長官一人。
最後,審判行刑結束後,長官對長老們的訓誡,以及長老們對屬民的訓誡,都直接說明了這一事實:這是一種以效忠庇護關係來成立的封建式支配。正如在最後的訓誡所指出的效忠關係一樣。聯邦共和國被視為領主,長官則為其代表,長老們效忠長官,長官保護長老,長老則是在村民認可下具有處理公眾事務的特殊身份。在上一章已談到,封建制度是怎樣從十字軍東征開始就深深的影響西方的殖民制度。在17世紀此時的北美、南美殖民地,到處都是封建庇護關係的開展,因此在此地發現這種封建庇護統治原理,其實並不令人驚訝。
網頁製作/林茗顯 2013/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