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亞細亞的孤兒》作初探
撰述人: 施正峰
認同就好比財富一般,當你擁有的時候,卻不需要它,但是當財
富已經耗盡,你才知道自己已經失去它了。
Identity is like wealth; when you have it you do not need
it, but when it is gone, you know you do not have it.
Klapp( 1969: x )
以吳濁流的作品為研究重心的論文尚屬可觀(1),但是以其民族認同(2)作研究對象的並不多 (3),而其中以政治學為切入點的幾乎是沒有,這除了反映出政治學者在方法學上強調「量化」與「重複實驗的可能」 (replicable) 的偏見,造成研究對象的畫地自限,也同時暗示著文學界對政治的嫌惡。
誠然,在過去統治者以國家機器來掌控社會,文學在無形中成為制約政治社 會化的工具,因此,掙扎著要維護自主性的本土文學對政治勢力的排拒,是可以 理解的。不過,站在民族運動的角度來看,文學雖然未有直接操弄政治權力的力 量,卻能發揮啟迪人心、建立民族意識的效能,其影響力之深遠,不是前者所能 比擬。
在本研究裏,我們暫且以《亞細亞的孤兒》為探索的時空範圍 (4),想要透 過小說中的主人翁太明來了解到底日據時代(5)濁老的民族認同為何?是日本人? 中國人?或是隱約成形的現代台灣人 (embryo modern Taiwanese)?抑或原生的 漢人 (primordial Han-Chinese)?而這些認同是如何的交織、矛盾? 這些是我 們想要解釋的應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
再來,我們嘗試著去探索到底是什麼因素促成濁老在認同上的心路歷程。有 三條主軸可供追溯,其一是血源(或文化)決定論,也就是藕斷絲連的中國在呼 喚,令人迷眩而無法抗拒;其二為權力結構論,即被統治者因為不滿加諸其身上 的結構性不平等,進而尋求認同上的出路;其三為共同的歷史經驗(或記憶)。
最後,由於文學不只是反應寫作當時的文化、或者是政治權力關係而已,它 還隱含著規範性的暗示,也就是什麼是理想的生活(或政治關係),因此,作品 本身的論述就是力量的泉源 (Zuckert, 1995: 189), 我們自然要嘗試著去挖掘 濁老明顯與隱晦的訊息:到底什麼是台灣人適切的國家認同?
所謂「認同」(identity) 是指一個人對自己的綿密感覺(a coherent sense of self)(Wheelis,1958: 19),它強調的是自覺(self consciousness) ,比如洛克 (Locke) 就認為「個人認同並不是來自對於實體 (substance) 的認 同,它只不過是對於意識 (consciousness) 的認同。 」而「民族認同」是一群 人在意識上有共同的自覺,也就是「我們」相對於「他們」或「你們」的獨特感 覺,同時這群人相信彼此休戚與共,在主觀上希望透過建立國家來保障共同福祉 (Shafer, 1972: 14-15; Gellner, 1983: 49);這裡,我們由「個人的認同」遞 進到「共同的認同感」。
在討論民族的文獻裡,一般會把其構成的因素分為客觀與主觀兩大類。客觀 因素又可歸納成 (1) 觀察得到的有形特色, 比如血緣、語言、宗教、或生活習 慣;(2) 無形的基礎則為共同的歷史或經驗。在眾多客觀因素中,又以無形(或 想像出來)的共同歷史經驗最為重要,因為它可以超越不同的有形特色而加以整 合。而主觀意識才是決定民族認同的關鍵。我們暫且把這些客觀與主觀的要素整 理成下面的樹枝圖 (taxonom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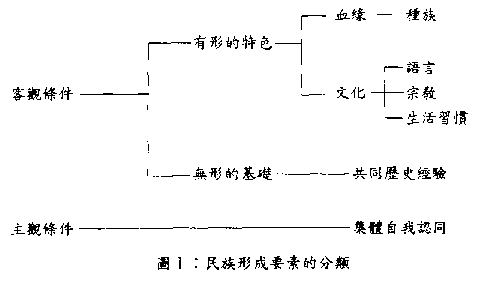
圖1:民族形成要素的分類
考察政治學、歷史學或社會學者的論述,我們大致可以把民族認同(或民族 主義、民族)的產生歸納成兩大類,一為原生的血緣論(或文化決定論),一為 權力結構論(或工具論):前者認為民族認同建立於一群人在客觀上有形的共同 文化基礎,比如語言、宗教、生活習慣,甚或共同的血緣(Isaacs, 1975);後者 則以為民族認同是因為一群人針對自己人在政治權力、或經濟財富上的分配不公 而形成主觀上的集團意識,而血緣或文化的特色只不過是動員的工具(Smith, 1991,1983; Snyder, 1976)。另外的第三類以研究文化的學者為主,他們強調無 形的基礎,也就是共同歷史、經憶(不管是真的或想像出來的)才是決定民族認 同的關鍵 (Anderson, 1991; Bhabha, 1990; Horton & Baumeister, 1996); Smith(1986: 2) 甚至這樣說:沒有記憶就沒有認同--儘管是選擇性的記憶。
上述三派的說法其實是不可分離的,因為光有有形共同特色,並不能保證彼 此能形成主觀上的一體感;同樣的,政治或經濟上的分配不均必須建立在共同的 文化或血緣基礎上,才有可能激發民族認同 6。至於結構上的不公平,我們認為 應該算是刺激民族認同形成的條件(contingent condition or contextual variable),而非構成的要素 7。 儘管著重的地方不同,這三派的共同點是主觀 上的集體自我認同為不可缺少的要素。
我們若要完整地納入結構性條件,我們必須再考慮心理學者的觀點。心理學 者大致追尋 Erik H. Erikson 的傳統, 以為認同除了建立在由個人、族群、或 民族的特色所組成的核心 (core) 外,更重要的是要由外在的社會、文化結構或 情境 (context) 的影響力所塑造。 認同是個人與社會環境的互動;惟有核心與 情境能獲得平衡,認同才能確保 (Graafsma,et al.,1994: 159-63)。 也因此, 認同不僅是內省後的自我想像,也是自己所投射給他人的意像,所以,認同是一 種互動的、 相對的社會關係, 也必須由他人的反應來獲得意義 (Klapp,1969: viii, 39-40; McCall & Simmons,1978: 65: Grotevant,et al., 1994: 10-12) 。既然如此,認同並非天生自然而且一成不變的,它必須在適切的環境下發展, 並且不斷地接受滋養與維護;隨著環境的改變,認同也必須不斷地作調整,以維 護其均衡 (Klapp,1969: 6)。也因此,任何認同都是建構出來的、獨特的、是歷 史的偶然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Connolly, 1991: 46-48)。 先前所提 的有形特色與結構上的條件,恰好可與Erikson 所提供的核心與情境作一對一的 相互對照與呼應。
這時,無形的基礎又要如何恰如其分地納入這個新的歸類?表面上來看,無 論是歷史、或是經驗,似乎都是客觀存在的,然而,它們與記憶一樣,往往是人 們選擇性認知的結果,甚或是想像或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在共同歷史經驗轉 化為主觀的認同之前,必須先經過人們的認知來加以篩選。同樣的,我們認為有 形條件(核心)與結構上條件(情境),也都必須經歷認知的過程,才有可能進 一步構成人們的認同。我們甚至可以說,共同歷史經驗只不過是過去的情境罷了 。結合上述討論,我們可以把這些因素匯合整理成下面具有序列含意的模型(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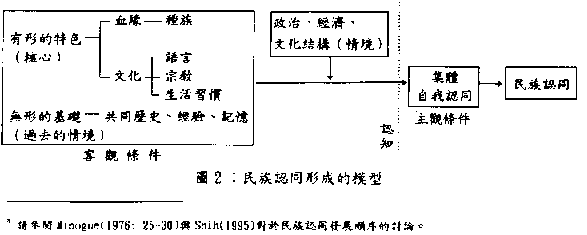
圖2:民族認同形成的模型
在《亞細亞的孤兒》(9)這本長篇小說裡,濁老透過男主角胡太明來敘述一 個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知識份子,如何在面對認同危機下追尋其自我認同。在這 裡,濁老採取傳統的固定認同(fixed identity)手法(10),把小說當作是他個人 的人生經驗,把自己化身為胡太明,藉著他來描述並評論故事中的人物與事件 (11),恰好是提供我們用來觀察認知的最佳素材。
我們將依據上面陳述的概念架構, 解構《亞細亞的孤兒》 12,把太明的認 知抽絲剝繭,看看到底在日據時代的濁老的民族認同為何?是漢人?中國人?日 本人?還是台灣人?這些多重認同之間的關係為何?是互不相干、互相競爭衝突 、抑或相輔相成的?他的認同是經過回答「我是誰」而自我認知取得(achieved) 的?或是經由別人回答「他是誰」而硬加 (imposed) 給他的?他的認同是如何 產生的?
對於持原生論(或文化決定論)者來說,認同的完成往往是必須透過你我( 或你們我們)之間觀察得到的不同有形特色來作辨識,其中又以血緣(種族)最 常被引為辨識集體認同的基礎 (Isaacs, 1975; Smith, 1986; 1991)。(13)
胡太明自認為建立在原生血緣關係上的民族認同,在暗戀同事內藤久子的過 程中一再提醒他自己:
「她是日本人,我是台灣人,這是任何人無法改變的事實。」 他想到這裡,胸間不覺引起一陣隱痛。(《亞》頁35)
這種感覺使太明覺得正視久子是痛苦的:
他的感情越衝動,越使他感到自己和久子之間的距離--她是日本人, 我是台灣人--顯得遙遠,這種無法填補的距離,使他感到異常空虛。 (《亞》頁 34 )
同樣的,久子也同意兩人的感情不可能有美滿的結局,「因為,我跟你.... 是不 同的.... 」(《亞》頁 60 )。當讀者還在納悶之際,濁老已急著跳出來告訴我 們:
什麼不同?這是顯而易見的,她當然是指彼此間民族之間的不同而言。 (《亞》頁 60 )
此外,因血緣不同而伴隨而來在文化上的差距也造成久子對本省人生活習慣 的負面刻板印象,以為太明不洗澡、愛吃大蒜。加上久子的民族優越感作遂,時 常在無意間以其「民族的智慧」來批評本省人,認為本省人是野蠻的。太明雖然 難堪,但是愛意使他寬容地詮釋,以為久子「無知的驕傲」不一定心懷惡意。相 形自慚的太明甚至以原罪來解釋:
自己的血液是污濁的,自己的身體內,正循環著以無知淫蕩女人作妾的父親 的污濁血液,這種罪孽必須由自己設法去洗刷..... (《亞》頁 36 )
根據 Wheelis(1958: 174) 的說法,一個人的認同要由其目標來定義,而其 目標則決定於價值觀,因此,我們若深入解析血緣與認同形成的關係,會發現父 母是關鍵的中介變數:父母本身的價值觀、希望、榮辱、或焦慮,都會反映在對 子女的期待;此外,父母更是提供歷史與共同記憶的直接來源。這些都是在子女 未出生之前就已產生,是子女必須作調適的情境,以建立自己的認同 (Graafsma,1994: 170)。
然而,長輩所留下來的記憶並沒有區分漢族與中國,無助太明建立滿意的自 我認同(14)。比如胡老人(祖父)雖然曾經「回到祖國 [ 中國 ] 去」(《亞》 頁 13 ),但是小說中對並此未作深入的交待,讀者也不清楚其真正的民族認同 為何。不過,中國至少是一個遙遠的記憶,是母親追述胡老人祖父時代大飢荒的 場域 (site) (《亞》頁 219-20 );相對的,高曾祖父糙米混合紅土做成土角 貯藏在夾層以防暴徒搶劫, 這個場景 (scene) 更使人印象深刻; 就整個事件 (episode) 來說,恐怕是共同經驗的傳承多於民族意識的訓誨。
也因此我們看到太明決定前往大陸任教,啟程前在大廳前祭拜祖先,看到樑 上懸掛的「貢元」匾額,不禁「使人對古代的傳統,引起景仰的心情」。乍看之 下,這一幕似要表現太明對中國的羈絆,但是由前來送行的親友口中祝賀他「一 代做官,三代富足」來看,頂多是像父親把它當作是考中進士或點翰林般的榮譽 罷了(《亞》頁 113-15 )。
同樣的,鴉片桶(伯父)提醒太明在江南有一座胡氏最大的祖廟,我們原本 期待的是藕斷絲連的氏族情感(15),誰知鴉片桶竟是為了它的財產多--如果當 上大官的太明前往燒香,可以賺一筆為數可觀的「貼膝禮」! (《亞》頁 116 )無怪乎太明也想贏回一塊「貢元」的匾額。不過,不管太明的考慮為何,他要 成為「埋骨於江南的第一人」(《亞》頁 173 )的決心, 除了冒險犯難的勇氣 外,還多少帶著對未曾謀面的祖國的無限嚮往。
果真首度看到紫金山的太明不禁嘆為觀止,因為「它比起台灣常見的叢山峻 嶺,的確巍峨多了,這種山嶽,只有在大陸上才能看得到的。」(《亞》頁 119 )友人曾提醒他「... 看揚子江,那滔滔的長流,它的流速多麼驚人,我們也必 須具有這種大河的胸懷。」(《亞》頁 120-21 )
懾於上海女子「高雅灑脫的趣味」的太明如此地合理化:
由於儒教中庸之道的影響,她們並不趨向極端,而囫圇吞棗地吸收歐美文化 ;她們依然保留自己的傳統,和中國女子特有的理性。(《亞》頁 121 )
迷惘的太明甚至在選擇性認知下認為「她們這種細緻謹慎的態度,和台灣女 性那股粗野的勁兒相比,真不啻有雲壤之別。 」(《亞》頁 122 )對於中國充 滿遐思的太明進一步推廣(16):
中國文學的詩境,似乎可以由女性表達出來,並且自然流露著儒教所薰陶的 悠久歷史,這些都是把古典型的高雅的趣味,活用於近代文明之中的實例。 (《亞》頁 122 )
如果說中國對太明有浪漫的魅力,對於其他人又如何?當太明成功脫險返回 台灣後,騷動的村人心存敬意,只因為太明是村內唯一去過大陸的人(17);而親 友也紛紛前來探詢中國的狀況(《亞》頁 184 )。 不禁令人懷疑他們關心的究 竟是故國抑或是異國情調?當我們再看到太明家人問他蘇州、西湖等地的風光, 以及胡文卿興奮異常地表示,如果這輩子能到大陸去觀光一次心願就夠了(《亞 》頁 184,187 ),我們可以判斷他們即使有殘遺的「祖國意識」, 也未嘗不是 把大陸當作香格里拉般憧憬罷了。
Klapp(1969: 23-29) 發現在現代化的過程中, 人們會因為舊傳統的衰敗, 失去象徵性參考點 (symbolic reference) 而進退失據,而產生認同需求的爆炸 。不可否認的,日本人帶來便利的現代化,尤其是在法治與交通上的建設,連胡 老人都必須同意(《亞》頁 10 )。身為中醫師的胡文卿也心儀日本人引進的新 教育,以為中醫不如西醫,並期待以知識解決切身的土地問題(《亞》頁 17-18 )。雖然胡老人在年輕時在祖國曾經接觸一些西洋文化,但是他的認識顯然與當 時飽受挫敗的中國人一樣,僅只了解皮毛;儘管他內心不服,甚至嗤之以鼻,以 為日本文化不過是西洋文化的支流,卻又莫明地心存恐懼(《亞》頁 14 ), 十足表現出認同遭到困頓的癥候 (Klapp, 1969: 11-13)。
表面上,胡老人耿耿於懷的是太明已經失去考秀才與舉人的機會(《亞》頁 10 ),似乎是往上流動的可能性 (upward mobility) 受阻,但更重要的可能是 胡老人對想像中「輝煌的」中國古代文化的鄉愁,比如春秋大義、孔孟道教、漢 唐文章、及宋明理學,那些他想藉傳統書院與漢文來傳給子孫的漢學,因此,堅 持太明到彭秀才那裡學漢文與四書五經。同樣地,彭秀才也擔心一旦雲梯書院關 閉,漢學就要淪亡了(《亞》頁 12 )。這種對傳統的依戀,正顯現他們在認同 上的困擾。
然而,太明並不太在乎是不是能考秀才或舉人。或許和多數被征服者一樣, 是失敗主義帶來的無力感,使太明「似乎茫然覺得那些都是滅亡的命運。」(《 亞》頁 13 )對回鄉參加彭秀才葬禮的太明來說,破敗的「雲梯書院」代表的是 「時代幻滅的象徵」。他雖然感慨,郤不願像老一輩的人「希望永遠深居在他自 己的思想樊籬中」,因為「我也有我自己的時代」,在冥想中,「似乎覺得燦爛 輝煌的時代,就在眼前向他招手。」(《亞》頁 56 )太明先後在國民學校、國 語學校師範部接受新文化,畢業後前往 K 國校任教。 根據他個人的觀察,他教 過的學生便有顯著的差異:
本省學生--目光淺近、氣質沉滯,
留日學生--見聞廣博、性情活潑,
彼此對談之後,益使太明不論在知識或見解上相形見慚,激起他強烈的留學 日本的意念(《亞》頁 53-54 ), 可見他對現代化的擁抱是經過理性的考量, 並非盲目的排斥傳統。
我們可以看到太明是 Smith(1983: chap. 5) 所討論充滿危機的「疏離的知 識份子」 (alienated intellectual) 或「過渡期的人」 (transitional man) :他們本身不得不拋棄傳統而接受西方教育,在自己的土地上反而成為陌生人, 也因此使他們對西方文化又愛又恨 (xxii-xxiv, 133-38)。這些人在心理上遭受 「殖民疏離」 (Serge, 1980: 141-42) 或是 Malinowski 所謂的「高等教育的 斲傷」 (Smith, 1983: xxiv),必須要去找回自己的認同。
民族意識於彼此日常生活習慣的摩擦中萌芽。在元宵燈會中,胡老人被日籍 (18)警察誤為亂民而用警棍重擊倒地,驚魂未定中感覺自尊心受損; 太明「覺得 非常悲痛,眼淚直流,怎麼樣也止不止。 」(《亞》頁 15-16 )又如全家到日 人開的照相館,母親不知上樓必須脫鞋而被日本婦人斥責,也使太明因為自己的 疏忽覺得不安而且憤慨。在這個插曲裡,父親為了要討個好彩頭而要太明忍耐, 太明也了解父親的苦心而忍氣吞聲。為什麼太明會遭到強烈的刺激?是異族的統 治?抑或政府的高壓?如果是滿洲政府又當如何?
由此可見,日常生活的衝突如果帶有民族的偏見或歧視,更是刺激民族意識 成長的溫床。 在 K 國校裡,校長把學校廁所的污穢歸咎本省籍學生教養不好, 因為本省人家庭的廁所本來就不乾淨。又如新生教養國語言表達能力有限,卻被 視為驕傲無禮,被觸怒的老師有恃無恐,體罰了學生還斥罵「沒出息!你還想做 日本國民嗎?」太明雖然心覺不平, 宛如自己也挨打般痛苦, 卻為了明哲保身 (19) 因而未採行動。(《亞》頁 47-48 )
稍早,工人在後山為了架設甘庶台車而挖胡家祖墳,母親抗阻不成反而被不 諳台灣話的日籍監工摑了幾掌,太明據理以爭卻被對方威脅飽以拳頭。而對這種 直接的肢體暴力,母親認為是飛來橫禍而息事寧人;太明雖然憤恨難平,卻替自 己找了一個忍氣吞聲的理由:「生平最痛恨暴力,對方既然要用暴力,當然不能 再跟他講理了。 」(《亞》頁 107 )太明不能安眠是有道理的,因為台灣人即 使上法庭也「絕對不能勝訴的」。心靈受到重創的太明
竟把這個問題漸漸地淡忘了。不過那絕不是真正地淡忘,而是把它埋葬在記 憶的深處,一遇心靈上受到新的創傷,那已經理葬下去的古老記憶,便全和 新的憤怒同時爆發的。(《亞》頁 108 )
不平等待遇是民族意識的催化劑。日本統治者透過公共政策積極推動,以國 家的力量把不平等的權力結構關係表現在政治地位與經濟利益的分配,使被支配 的台灣人對自己的認同不滿意,必得要去尋求出路。 Klapp(1969: 14-16) 認為 在這種情況下的認同即使遭到歧視,反而能孕育出強烈的認同感,總比空無一物 來得好。
剛來到 K 國校的太明立即發現日、台籍教員之間的芥蒂。 對台籍教員來說 ,日本人校長召集日本教員在宿舍裡歡迎日籍新老師內藤,不啻是違反「日台平 等」的精神。然而,涉世未深的太明並沒有不滿,反而認為陳首席與李訓導的抱 怨只不過是借題發揮,要來煽動他;他甚至認為背地裡批評校長是有失教育者的 風度(《亞》頁 27-28 )。
迨台籍教員前來他的宿舍私下舉辦歡迎會,太明下意識更覺得這種別苖頭的 作法一定暗藏著某種陰謀詭計,擔心他們會進一步滋事,因此既感不耐煩又苦惱 。席間同事大發厥辭,紛紛議論校長的差別待遇,尤其是只准日籍教員出差。太 明卻寧願相信同事只不過藉此打牙祭,並不太在意李訓導的激烈抨擊,他甚至以 為同事的肚量過於狹窄(《亞》頁 30 )。
為什麼太明與眾不同?可能是他過去受教育的過程中,與日本教員的關係一 向融洽吧?(《亞》頁 25 )(20)如果真如李訓導所揶揄,太明已被日本人成功 奴化教育為「大國民」(走狗),那麼他就永遠不必苦惱了。然而,當晚他竟也 為了日、台籍教員間的不平等待遇而失眠(《亞》頁 30-31 )。
暗戀久子的太明開始為了前途而正視同事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比如陳首席 訓導雖然年資較深,校長卻提拔伊籐訓導為教務主任,果真是因為他的「舊頭腦 」?使太明痛苦而絕望的不只是血緣上的「裁判」,而是深一層考慮後隨之而來 的各種難題。首先,身為台灣人國民學校教員是「永無出頭之日」的,當然是沒 有能力供養「日本女子久子所需求的高度生活」,想到這裡,「太明所有的希望 頓時都變成泡影了。」(《亞》頁 35 )
在教學上(21),太明也開始懷疑,為什麼日本小學可以不用體罰,台人國校 卻必須強迫學生以贖罪方式罰跪水泥,甚至「暴力制裁」?為何日人小學可以正 常教學, 台人學校卻必須專注農業教育?(《亞》頁 48-49 )家長林氏因伊籐 導師拒絕替小兒特別指導 22 而轉求太明,舐犢情深竟使他「不禁燃起正義的火 炬」(《亞》頁 38 )。台籍學生的升學出路也面對結構性的歧視。雖然「日台 共學制度」揭櫫一視同仁,但是在皇民化不夠、家庭日語化不夠的種種理由下, 台灣人的入學人數被限制,造成台籍學生之間的「蝸牛角之爭」,再怎麼努力都 是徒勞無功的(《亞》頁 72,37 )。
曾導師事件促使太明檢討自己明哲保身的哲學。校長平日以語言教育來非難 本省籍教員,以為不懂「國語」(日語)的人缺乏「國民精神」,要求本省籍教 員以身作則, 要率先把自己家庭「國語化」,否則不配擔任教員(《亞》頁 47 ),其同化的企圖明顯。在一次檢討會上,有人指摘本省籍教員必須為學日語發 音不準負責,引起台、日籍教員間的緊張。這時,曾導師揭竿而起:「如果說本 省籍教員的日語不好,試問我們本省人難到都是天生懂日語的嗎?」(《亞》頁 49 )曾導師趁勢挑戰校長平日口頭掛著「日台平等」, 但是教職員名牌卻是把 日本人排在前面,未依照職等排。他說出眾人不敢講出來的心裡話:
真正的「日台平等」是不應該有偏見的,也不應有色彩的!(《亞》頁50)
開發中國家的政府,為了要有效統治與推動公共政策,它必須想辦法以行政 與法律來滲透社會,否則會有「滲透的危機」 (crisis of penetration)(23)。 政府的滲透能力最起碼表現在稅收、徵兵、以及控制偏差行為上 (LaPalombara, 1971: 209),但是台灣人並不願全盤接受日本人的統治(24),比如胡老人雖然肯 定日本人減少盜匪,郤又抱怨稅賦沉重(《亞》頁 10 )。
太明母親與水利合作社視察員的衝突,以及他自己與合作社台籍辦事員及社 長了新開墾土地的課稅而衝突一事(《亞》頁 213-16 ),雖然可以用「台灣人 欺侮台灣人」, 也就是反殖民的角度來看 25,但也未嘗不可使用民間抗拒因素 滲透的觀點來詮釋。台灣人對於現代國家機器的畏懼,也可以從苗栗三叉河(三 義)民間山林強制收歸事件看出來,因誤傳特許三丼財團為收歸官有,大家搶著 砍下木材(《亞》頁18 )。同樣地,米穀檢查員的無度需索(《亞》頁194-96) ,原先可解釋為公務人員的貪污,但是在此三人為日本人,以及米店老板不諳日 語的安排下,讀者自然會以反殖民的感情來看。
國家滲透的具體表徵是公共政策的推動,尤其是農業的現代化,但是在台灣 人眼中,難逃被視為殖民者的壓搾。以「正條密植」政策來達到增產的目的,這 種決策原本是無關殖民與否,但是使用毆打或罰跪水泥地來推行(《亞》頁217- 18),自然會引起民怨。
如果純粹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為了保護台灣的製糖事業而實施「地域限 制政策」(26),為了使農村剩餘人口轉換為勞工而採取「米穀管理法」來壓低糧 價,以及嘉南大圳灌溉區的「三年輪作制」,是應該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政治活 動家與農民的眼中,這些都變成殖民者抑制「土著」(native)資本、壓搾農民血 汗的工具(《亞》頁72,193)。我們不禁懷疑,這些政策如果是由本土政權來推 動,是否還會有如此強烈的民族主義反彈?
在戰爭期間,台灣和日本國內(27)都實施嚴格的「經濟統制」制度,本島企 業家飽受限制(《亞》頁231)。此外, 統治政策在台灣更是用來保護日本人的 工具,使統制機構變成日本老官僚的養老院,尤有甚之,統制機構的重要職位由 日本人佔據(《亞》頁129),不信任台灣人的心態昭然若揭。以太明任職的[糧 食]納入協會為例,儘管日籍主管尸位素餐,相較之下,本省人品格高尚、學驗 兼優,但是「本省人究竟是本省人,連個委任官都當不到」,委屈求全的太明可 以真正體驗到「本省人悲慘的遭遇」(《亞》頁235-37)。這刻骨銘心的共同命 運,正是台灣人集體認同的形成基礎。
皇民化運動也就是同化政策,日本人希望透過它來確保台灣人的忠誠度;只 有通過一次又一次考驗的人,才有資格當「皇民」,否則就是「非國民」。被殖 民者可以採取的積極對策有三28:接受同化;浪漫地回歸傳統;或是進行改革, 建立新的認同 (Serge, 1980:139-40; Smith, 1983: 136-37)。對於民族運動者 來說,他們必須進行艱苦的三面作戰,同時要對抗殖民者,復古派,以及同化派 (Serge, 1980: 42)。
其實早在戰爭之前,就有台灣人積極把自己皇民化。比如當預備警員的志遠 堂兄就一身日本味,開口日本話、抽日本菸、用日本肥皂洗澡。哥哥志剛更是徹 底日本化,食衣住行都摹仿日本人:吃日本麵、穿和服去神社參拜、房屋改建為 日本式29(舖榻榻米、建日式廁所)、改掛日本畫軸、家裡設神龕、甚至改姓「 古月」(《亞》頁13,187,192-93,197-98,211)。「皇民派」的人不只要過「和 服」及「味噌湯」的生活,名字還要日本化,家庭也要「國語化」。
對於日本殖民政府來說,為了要徹底同化台灣人,必須剝奪台灣人的精神武 裝,當然要消滅台灣語言。然而,台灣人自己的立場又如何呢?首先的考慮是方 便,胡文卿與志達便以為官廳都用日本話了,「不懂日本話的簡直就是傻瓜」 (《亞》頁17)。在這裡,同時隱含的是日本話為吸收西洋新思潮的不可或缺工 具。改陳姓為「東」的鄉公所秘書如此合理其皇民化:「我們為了後代子孫著想 ,熬過這段過渡時期,就可以作個堂堂正正的日本人了.....」(《亞》頁211- 12)李導師不只實踐「家庭國語化」,還在父母的反對下率先改姓為「吉村」, 因為「我認為自己這一代的艱苦,如果能換得子孫的幸福,還是值得的」 (《亞》頁270)。
皇民派所採取的這種自我殖民的代替策略 (vicarious),是希望透過主動的 同化來改變自己,以打破殖民者所加的歧視障礙(Serge, 1980: ix,8-9; Klapp, 1969: 45)。表面上是為子孫謀幸福,其實是希望皇民化以後,能獲得和日本人 一樣的公平待遇。比如說,不改姓的學生,中學入學考試的錄取率較低;即使考 上的人,日後也會被學校強迫改姓,不如自動改姓,以提高錄取率(《亞》頁 212)。 甚至在戰爭期間,「國語家庭」與日本人享有特權,可以分配到一般百 姓所繳交的食物(《亞》頁253)。又如在戰爭期間盛行「瓦全論」。傳聞為了 要移民日本人到台灣,殖民者要把台灣人遣往南洋去,因此台灣人「寧為瓦全, 不為玉碎」,自然要皇民化,否則就不能抬頭了(《亞》頁228-29)。
然而,儘管主張皇民化的人再如何誠心誠意,卻仍然無法如願與日本人平起 平坐。事務員中島雖已皇民化二十多年,卻永遠昇不起來,因為若按年資來排, 勢必讓他爬到日本人頭上,因此只能以雇員終老(《亞》頁237-38)。同樣的, 吉村發現自己拼命地往皇民化走,結果卻是越走越遠(《亞》頁270)。苦悶的 吉村在自省後發現,原因在「別人有他們悠久的歷史和傳統關係,我們卻沒有, 這種障礙是無法打破的」(《亞》頁270-71)。反對皇民化的藍律師在譴責前者 忘了本國傳統之際,更強調即使外表能皇民化,彼此的血統不同依然無法解決 (《亞》頁228)。相反的,中島謙卑地以為是自己實行皇民化不夠徹底才無法 昇官(《亞》頁238)。侄兒達雄甚至真誠地相信台灣人必須奉身聖戰,才能通 過是否成為皇民的最後考驗(《亞》頁272)。
反皇民化的人看法又如何呢?志達雖人稱「大人」,卻人緣不好。是因為人 們對他所代表的政治權勢作反抗,還是嫌惡他的皇民化?妹妹對於當保正的志剛 不只挖苦,還彼此為皇民化而吵架(《亞》頁188,197)。在太明的想法裡,為 了食物配給而改姓的人委實動機不純正,有如「便所蠅」、「紅頭蠅」般投機; 而那些附和殖民當局政策的台大御用教授則被斥為豺狼(《亞》頁212-13,265) 。母親阿茶甚至詛咒配合搜糧的兒子志剛為「短命鬼!吃日本屎的!」 (《亞》頁222)
總之,太明認為皇民化運動是閹割台灣人的致命傷,嘲弄為皇民化而努力的 人是愚笨的,「到頭來無非是一齣人間話劇而已」,不只是台灣人的悲哀,甚至 是「面臨滅亡的民族悲劇!」(《亞》頁 271,213,219 )是怎麼樣的民族? 他 沒有說出來。
然而,太明到底是浪漫的30,因為:
中了這種政策毒素的,畢竟只有一部分利令智昏的台灣人,其餘絕大多數的 台灣同胞,尤其是在廣大的農民之間,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 。他們雖然沒有知識和學問,卻有和鄉土發生密切關係的生活方式,而且那 與生俱來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為名利、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度。他們唯 其因為與鄉土共生死,所以決不致為他人所動搖。(《亞》頁 229 )
誠然,皇民化是無止境的考驗,尤其是在戰爭期間所進行的「國民精神總動 員」下,任何不配合政策的人都不配作「國民」,比如不配合糧食增產、或私藏 金、貯米,都是「非國民」的罪嫌,甚至連台灣裝與漢服都被視為「敵性」的服 裝(《亞》頁 215,190-91,220,198 )。在國家以這種積極的方式滲透下,太明 的樂觀是否有其他理由?
太明真正面對認同問題的正面挑戰,是在來到東京留學的第一天,藍姓友人 好意告誡他最好不要承認台灣人的身份,建議他佯稱來自九州福岡或雄本。為什 麼?濁老並沒有交待,不過太明從此嫌惡友人。到底是因為太明不喜歡這種自卑 的作法,還是因為他發現台灣人連日本下女的地位都不如而覺得屈辱(31)(《亞 》頁 69)?第三天太明立即搬出友人家,「從那天起,他便不再隱瞞自己是台 灣人」,而日本房東母女似乎不把他當外人(32)(《亞》頁 70,74 )。
即使太明從此面對日本人時都能夠坦然自認為台灣人,但是在遇到中國人時 呢?答案是否定的!太明隨藍參加留日中國同學會時,又面對類似的身份問題。 席間北平話不流利的太明不小心漏出台灣話(客家話)來,被誤以為是來自中國 的客家人,但是他還在躊躇,並不敢馬上揭露台灣人的身份(《亞》頁 76 )。 迨一名來自廣東番禺的學生向太明自我介紹,他才大膽說出自己是台灣人,卻引 起全場中國留學生嘩然。
令太明不解與憤怒的是中國留學生對台灣人的輕蔑與歧視,而騷動的原因是 會場裡頭的中國人視台灣人為間諜(《亞》頁 77-78 )。 藍的解釋是因為台灣 人在廈門藉日本人力量狐假虎威,要怪的是日本人的離間政策;太明對於這種說 法無法釋懷,當然不願參與反日的政治活動。
其實,太明對於忠誠度遭中國留學生懷疑,應該在心裡上早有準備的。早在 他擔任教員時,就有師範學校早他六、七期的學長向太明警告相同的經驗:
台灣人到任何地方去,依舊是台灣人,到處受人歧視,尤其是中國大陸,因 為排外風氣甚盛,對於台灣人也極不歡迎。(《亞》頁 53-54 )
太明當時雖然感受到這種歧視而一度動搖留日的念頭,但似乎尚未察覺自己 的民族意識, 懵然中決定到日本本土追尋認同的答案: 「試試看吧!總而言之 ...... 」(《亞》頁 54 ),想不到竟遭到中國人在認同上的挑戰。
不知是否因「祖國意識」的作祟(33),太明終究還是來到南京。曾姓友人好 意告誡他在面對中國人時不要公開身份,因為「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別人都不 會信任我們。」曾並沒有說明為什麼連中國人都不會信任台灣人,只抱怨道:
命中註定我們是畸形兒,我們本身並沒有什麼罪惡,卻要遭受到這種待遇是 很不公平的,可是還有什麼辦法?(《亞》頁 120 )
在濃厚的無力感中,曾一廂情願地建議台灣人「必須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 不是天生的『庶子』,我們為建設中國而犧牲的熱情,並不落人之後啊!」(《 亞》頁 120 )自認為「蕃薯仔」的太明雖然不甘心台灣人必須忍受「別人」(34) 的侮辱,除了感到黯然神傷,他並沒有懷疑台灣人為什麼必須向中國交心,而不 是為台灣來犧牲。
果不其然,太明被人密告是台灣人而被國民政府以間諜的嫌疑逮捕。太明坦 承台灣人的身份,並且竭力表白建設中國的誠意,卻不能改變當局的既定政策 --不能信認台灣人(35)(《亞》頁169-72)。這次入獄使太明頓悟同時有許多 任職於國民政府的台灣官員,和他面對一樣的命運,毫無選擇於地被捕。為什麼 只要是台灣人就會遭到相同的際遇呢?曾先前回答:「這不是別人的事,而是有 和自己的命運有關係的問題。」(《亞》頁172)這種命定論(deterministic) 的說法並不能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但是至少提醒太明,不願接受台灣人的認同 (identify with)的不只是異族的日本人,連原本以為是自己人的中國人都排斥 台灣人。太明又一次經驗台灣人的共同命運。
越獄的太明來到下關碼頭,要求搭日本郵船偷渡上海,這時,他的認同又遭 到一次考驗。 原先,太明是把日本視為敵人的(《亞》頁 163 ),迨遭中國人 追捕後,才又承認自己是日本籍人,轉而求助日本人。由日本籍船長的眼光來看 ,諸如太明這種台灣人的作法是投機的,但也只是冷諷熱嘲,並沒有拒絕他;而 上了船的太明,竟然「就像到故鄉的船上一樣,內心立刻安定下來。」(《亞》 頁 179-80 )當時的太明是否有開始思考究竟誰是敵人?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 呢?
避難上海租界地的太明發現台灣人的日本人身份並不可靠,因為日本憲兵認 為台灣人與中國人並沒有什麼差別,以為租界地內的台灣人都是恐怖份子,因此 開始公然逮捕他們。日本憲兵的推斷應該是合理的,因為幽香的姐夫李雖同情太 明,卻是想利用太明的身份從事「政治工作 36 」(《亞》頁 180-81 )。太明 似乎是毫無抗拒地接受李的嘲諷:
我很同情你,對於歷史的動向,任何一方面你都無能為力,縱使你抱著某種 信念,願意為某方面盡點力量,但是別人卻不一定會信任你,甚至會懷疑你 是間諜,這樣看來,你真是一個孤兒。(《亞》頁 180 )
太明雖然發現「台灣人變成夾縫中的人物」、「台灣人的歸依正遭逢嚴重的 危機」,但是他的自省力顯然不足,依然把台灣人被區分為敵友兩流的這個事實 ,悲憤地歸諸於是日本人既定的政策(《亞》頁 181 )。
到底誰是敵?誰是友?是誰的敵?是誰的友?難到台灣人在發展屬於自己的 認同的過程中,連一點選擇的機會都沒有?或許,太明認為的確沒有機會;甚至 ,太明以為認同不是可以選擇的(37)。所以,他只能以自己沒有作虧心事來自我 安慰(《亞》頁 181 );他並不了解認同無關良心 (38)、理性、或是公義,而 是如何面對情境來定義出滿意的自我出來 (Klapp, 1969: 14-15)。 無怪乎安然 返台的太明,稍後聽聞在大陸的台灣青年陸續被遣返台灣下獄,他會視為晴天霹 靂而感到異常憂慮(《亞》頁 190 )。
其實,太明在上海住過一個月左右,對於中國大陸的熱忱已逐漸降低。他雖 然感到不安,卻未加以深究,只以為是自己對中國的認識太膚淺之故(《亞》頁 120-21 )。語言上的隔閡的確使他挫敗,因為原本他以為台灣話(39) 也是中國 話之一,而他雖諳廣東話與福建話 40,卻發現與國語不通(《亞》頁 122 )。
不過,他對於中國的負面印象隨著他停留時間拉長而累積著,比如在上海往 南京的火車上,少女不脫鞋而站在椅上去拿行李(《亞》頁 124 ); 又如對於 麻痺異鄉人的中國澡堂的排斥(《亞》頁 129-30 )。最使他痛心的是發現中國 人的投機,竟然預期中國遲早會減亡,大家為了飯碗因此瘋狂地學習日語(《亞 》頁 157-61 )。
但是這些都還不足以切斷中國對太明的羈絆。二度到中國的太明,這一次是 被徵兵往廣東。廣州居民對腰掛單刀的太明懷著敵意,他的反應是「很想對他們 表明自己的心跡」。到底是怎麼樣的心跡?是血濃於水,抑是被迫當日本人的無 奈?濁老並沒有明確表達,只藉著太明表示「那究竟是不容易做到的事,而且也 不一定能博取別人的信任,因此反而不如保持痛苦的緘默好些」(《亞》頁 202 )。我們好奇的是:為什麼台灣人一定要向他人表態?
到底太明認同的地方是那裡?在他遭受挫折後,他想回去的故鄉(homeland) 是那裡?是日本?中國?還是台灣?濁老給我們的訊息並不清楚,或許,原本太 明的認同就是在搖擺之中。而這些多重認同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彼此相容、相斥 、抑或不相干呢?如果只考慮日本與中國(41),有下圖的幾種可能性(42):

圖3:認同的競爭
對於留學日本時的太明來說,台灣是故鄉,是故國 (home country) (《亞 》頁 65, 78-79 ), 甚至他前往中國大陸之前許下宏願「不成功絕不重歸故土 」(《亞》頁 115 ),仍然是以台灣為故土。 不過,對於祖父來說,中國是祖 國(《亞》頁 13 ),而對妹夫林岳東來說, 卻是外國(《亞》頁 116 ),分 別是上圖a與c部分, 互不相容。 太明自己也把中國視為祖國(《亞》頁 272 ),也就是a的部分,因此把大陸之行視為「歸故國」,只不過惟恐遭忌而改為 中性的「遊大陸」(《亞》頁 117 ), 我們自是無法抹煞太明的「祖國意識」 (43)。
一直到太明在中國以間諜罪嫌下獄後,他又對台灣產生思慕之情:
這次嫌疑洗清以後,一定要回到可愛的故鄉去,無論怎麼樣艱苦也願意忍受 ....。可是,誰知道究竟是否能重回故土呢?(《亞》頁 174 )
這與他當日離台所下的豪語, 「不, 他根本就不算再回來了」(《亞》頁 113, 115 ),不可同日而語。 為什麼?在獄裡,他想到的是萬一被處死,將成 為孤魂,永遠不能回鄉(《亞》頁 176 )。 懷鄉之苦,竟連幫他偷渡的日本郵 船都像故鄉(《亞》頁 180 )。 回想起來,太明的首度大陸之行竟是「在外面 漂泊流浪」(《亞》頁 187 ),中國已儼然退到「異鄉」的地位, 而他的認同 流向b,甚至是c的部分。
中日戰起,被強徵入伍派往廣州的太明卻因精神刺激而遭遣回台灣。當時台 灣人趁時局之變絡繹大陸之行,太明的父親便認為這是「發展大陸」;太平洋戰 起,香港、新加坡淪陷,台灣人分享日本的榮耀,企盼前往南洋發展。太明卻持 不同看法,以為這是日本人的宣傳之毒,因為那些在日本人軟卵翼下的台灣人為 了名利出賣「同胞」,而「民眾44」當然知道他們的作為(《亞》頁224, 230, 233)。 太明甚至認為有志的台灣青年與知識份子應該到大陸去發展,去追求「 沒有矛盾的生活」,不能再袖手旁觀(《亞》頁231-33),可見他對中國難以割 捨。難到太明前去中國就不再有矛盾,不會再被排斥了嗎?他到底是要站在什麼 立場來參與?
是什麼因素使太明又萌生回大陸的念頭? 或許是思念妻女(《亞》頁 246 ),或許是在南京時,張姓參事鼓舞的愛國主義(《亞》頁 157-60 ),或許是 在廣州時, 目睹中國青年慷慨就義而激起的中國民族主義(《亞》頁 205-6 ) 。當時擔任審問翻譯的太明:
每當他眼見那些愛國青年從容就義,捨身殉國時所表現的至高無上勇氣,使 他感到莫大的威脅。他們臨刑雖然非常鎮定,但太明的精神卻發生了激烈的 動搖,良心上也遭受極大的譴責!(《亞》頁 206 )
當然, 日籍雜誌社同事佐籐(45) 也提供太明一些反戰 (pacifist) 的思考 (46)(《亞》頁 256-66 ),因此眼見侄兒達雄立志效忠聖戰,以為是受騙誤入 歧途而心痛。他覺得那些高唱軍歌招搖過市的青年已喪失人性,面對那些被訓練 成機械化、傀儡化的青年就不寒而慄(《亞》頁 272 )。 那麼,那些慷慨就義 的祖國青年,是否也是同樣受騙而不自覺?濁老並沒有明顯答案。這時,我們看 到濁老借著發瘋的太明把箭頭指向墮落不堪的「現代國家」,大加撻伐納粹德國 與日本藉國家民族來合理化其殺戮與征戰(《亞》頁 272-74 ),反倒模糊了他 原先所嘗試在國家認同上的釐清(47)。
總之,太明的認同是依違於台灣(故鄉)與大陸兩地之間,同時又制約於中 國(祖國)與日本兩國之間,高度流動而不自知。
在《亞細亞的孤兒》這本小說裡,濁老筆下的胡太明是一個飽受認同危機的 知識份子。求職不順與愛情挫折使他陷入苦悶;親友及自我的期待加深了相對剝 奪感;使他憤懣的是自己空有能力卻不能發揮。更嚴重的是他在不同的認同拉扯 下感到絕望與痛苦。
原先,太明自以為他的認同是天生命定,一定要建立在原生的漢人血緣與中 國文化上,但是卻逐漸發現這些並無法抗拒權力結構的侵蝕。不論是躬自內省、 明哲保身或是逃避現實,都無助於解決他在認同上的苦痛。原本,這正是他勇敢 面對這些認同挑戰的契機,但是夢幻般的中國卻如幽靈般不斷地在呼喚著他,使 他牽腸掛肚,無論如何也要試試看祖國是怎麼樣。太明兩度進出中國大陸,一次 囿於血緣上的困惑而興緻沖沖地自願「回歸」,一次徵兵前去,終於發現他所認 同的中國並不比日本殖民者更接受他。沮喪的他不得不承認台灣人己經無處可逃 ,終究必須自我切斷那風雨飄搖、有如夢魘般的中國羈絆。
面對日本人統治者,太明雖然了解癥結是他們把不平等的權力結構硬加在台 灣人身上,有如枷鎖而不得翻身,卻不禁產生劣等情結 (inferiority complex) ,懷疑自己是否有問題,甚至怪罪自己的血統是否污濁。太明因此不時陷入困境 、容易受傷,對自己的命運感到無助,卻又不甘如此罷休。這種痛苦的自覺,正 是尋求認同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經歷。
他究竟應該怎麼才好?他到底應該往那裡走呢?太明一再地問自己。和所有 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份子一般,太明對於自己的世界充滿著疏離感,因此是不可 能把自己投入時空倒轉的復古運動;同時,他也不願意和熱衷皇民化的運動者一 般樂意接收日本人強制指定的認同,偽裝自己可以變成日本人。
Neubauer(1994: 134) 告訴我們,健全的認同應該是經由選擇而來,那麼, 到底什麼是妥適的台灣人認同?濁老並沒有在這本書告訴我們,他只隱約表示「 由此可見一個人如果除自身以外一無所有,則絕不能藉改姓而取得新的人格」、 「為了要把自己從這種可憐的境遇中解救出來,切望能早日建立一個獨立的家庭 」(《亞》頁 126-27, 212 )。 兩者都有積極地去建構台灣人自己的集體認同 的意思:前者直接反對日本的皇化運動,後者則似乎以作食客的可憐暗示著脫離 中國的弦外之音。
中國之行並非罔然,因為他體認到作為一個台灣人,不論到那裡,命運都是 悲哀的;同時也覺悟到他個人的認同,惟有透過集體的方式才能獲得肯定。正是 這種共同命運感孕育了日後台灣人的民族觀,使台灣人徹底覺悟自己有權利存在 ,並且有權利建立一個主權國家。因此,我們並不認為太明的中、日之行是一種 逃避;相反地,我們以為他的嘗試宛如 Klapp(1969: 41-43) 所述探求聖杯的十 字軍 (Grail hunter) 的作法,因為認同非得要先經過陣痛才能浴火重生
人生的目標如果是自我實現的話,那麼,堅定的自我認同應如指南針,指引 前進與行動的方向,並提供自我評估的標準,因此,認同是必須經過實踐來完成 的,而且必須不斷地去贏取。太明的選擇是勇敢地去面對認同問題,透過集體的 認同投射來追尋 (seek) 自己的真正認同。誠如 Wheelis(1958: 205) 所言,認 同不是失落了(lost),而是不適合了(outgrown),因此不是去尋找(search) 或恢復(recover),而是去創造(creat)與完成(achieve)。在這同時, Wheelis(pp.20-21) 建議我們要先要忘懷過去,才能重新建構未來。因此,濁老 的「台灣人意識」之建構,要到下個階段對中國幻滅之後,也就是《無花果》與 《台灣連翹》時才算完成
註 釋 1 請參詳文後所附中文參考文獻
2 民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又譯為國家認同,其實兩者同義,因為 民族的意義就是一群人要共同建立一個國家,叫民族國家(nation-state), 所以也是以國家來作認同的對象。不過,在漢文裡,民族往往有種族(即血緣) 的涵意
3 有深入探討的是彭瑞金 (1978; 1986; 1995)、 陳映真 (1977)、 林釗誠 (1978)、宋冬陽 (1985)、及張良澤 (1984; 1975), 而張文智 (1993)、顏元叔 (1973)、尾崎秀樹 (1973) 則稍有論及
4 吳濁流經歷日本與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同時又有中國(大陸)的經驗; 而 太明的故事未及國府時期
5 如果我們要全盤了解濁老的民族認同, 將來必須把研究的對象擴及《無花 果》與《台灣連翹》
6 其他可能的認同有階級或性別
7 既然如此,結構性因素就不應該列入圖1
8 請參閱Minogue(1976: 25-30)與Shih(1995)對於民族認同發展順序的討論
9 以下的引證用簡寫《亞》來代替
10 也就是作者等於敘述者;相較比來,現代的敘述方式則由外人觀察,即作 者不等於敘述者,稱為分散式的認同(diffused identity)。請參考 Neubauer(1994)
11 而《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則為濁老的自傳。在《無花果》裡,濁老不 只是滿足於故事的敘述,更是跳出來臧否人物,毫無掩飾。《台灣連翹》的風格 相仿,批判的性質更加強烈,尤其是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理,不光是對歷史作見證 而己,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赤裸裸的論述了
12 濁老的中、短篇小說亦有日據時代經驗者, 比如 < 陳大人 >、< 水月 > 、< 功狗 >、< 泥濘 >、< 先生媽 >、< 路迢迢 > 等等, 全部都收於《功狗》 ,請參考瀧川勉 (1974) 的簡介;有關中國經驗的散文則收於《南京雜感》
13 Isaacs 用的字眼是 nationality,而 Smith 用的是法文 ethnie ( 或英 文 ethnic community)。 請參考 Smith (1991: 20-21) 對於 ethnie 與 race 的區隔
14 愛爾蘭人在民族認同的建構過程中,一直爭辯到底祖先留下的記憶是否有 所助益 (Murphy, 1991: 79)
15 鴉片桶的正名為胡傳統(《亞》頁12)
16 太明對於中國藝術的評價就比較不帶感情。他雖然認為許多古代翰墨「把 中國故有的高深文化精神,充分地表露在幽香的墨痕之間」,卻也能體會出中國 近代繪畫「只在悠久歷史偉大的傘下蔭蔽,不出其蔭影一步。」(《亞》頁 142 ) 17 濁老似乎忘了胡老人也去過大陸
18 我們作如此猜測是因為警察說「馬鹿」(《亞》頁15)
19 彭瑞金(1978)對於太明的個性有相當尖銳的批判
20 太明因個性忠厚而普遍受其國校老師喜愛,尤其是幫獨身的堀內老師作飯 (《亞》頁 25 )。不過,濁老並沒有交待太明在國語學校師範部的情形
21有關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的教育政策與台灣人的抗拒,請參考 Tsurumi (1979; 1980)
22 由於伊籐指導那一組並沒有課外補習,那麼,究竟他拒絕特別指導是常態 ,或者是歧視?我們無法確定
23 除了滲透的危機外,開發中國家在走向現代所面臨的危機還有認同、正當 性、政治參與、及分配。請參考 Binder 等人 (1971) 的討論
24 Myers 和 Peattie(1984) 所編輯的書對於日本的殖民政策有詳盡的探討 ,而 Chen(1970) 則特別比較了日本在台灣與朝鮮的政治控制手段
25 弦外之音就是這些台籍公務人員為買辦
26 也就是禁止蔗糖自由運銷
27 濁老用「國內」來指日本本土,是否暗示台灣為「國外」? 28 請參考 McCall and Simmons(1978: 92-97) 對於其他消積性策略的討論 。另外,請參考 McNamara(1986) 與 Chen(1972) 的論文來比較台灣人與朝鮮人 的不同反應 29 志剛嫌紅色太中國味,因此牆壁漆成日本風味(《亞》頁197)
30 Kohn(1944)、 Snyder(1976)、與 Minogue(1967) 對於 19 世紀日耳曼盛 行的浪漫主義有深入的介紹
31 請參考 James Baldwin 對美國黑人因為不滿意白人所硬加的認同而不敢 說出自己的身份所作的描述 (Klapp, 1969: 16)
32 太明認為東京人溫文、熱心,說話不像在台灣的日人般粗魯,連警察看起 來都很和氣(《亞》頁 68 ),但不知是否只是對外來人表面上的客氣而已? 33 照彭瑞金 (1978: 183) 的看法, 太明是以「孤兒」之身,懷著「尋母」 的心情而來的
34 在這裡,尤其是指中國人
35 二次大戰期間,日裔加拿大人與美國人面對類似的忠誠問題而被集體拘留 於集中營
36 應該是指地下工作
37 Grotevant 等人 (1994: 1-3) 在探討認同發展的過程時, 使用「有機會 選擇與否」及「由自己或他人來決定」兩個面向來衍生 2*2 種可能
38 濁老在其他地方作了類似的表白,比如頁183、237
39 在此意是指客語
40 指閩南話或Holo話
41 這裡的中國只是概括之詞,與漢族這個概念有相當程度的重疊
42 請參考 Boyle(1991: 71-72) 對於北愛爾蘭人國家認同的探討。本圖的靈 感來自Lasker(1982) 對於以色列的猶太人(Israeli) 所具有的猶太 (Jewishness) 與以色列 (Israeliness) 成分的解析
43 也就是中國意識。論者一般都以相互排斥的方式來看民族意識(或認同) ,比如陳映真(1977) 與古繼堂(1992) 強調濁老的「中國意識」, 宋冬陽 (1985) 與陳嘉農 (1987) 則專注其「台灣意識」
44 這裡的「同胞」與「民眾」都是指中國人
45 佐籐的基本態度其實是反台灣人的,因為在他眼中,不論是衣著華麗的日 本女人或是日本紳士,只要脫了外衣,「也就和本省人一樣的令人生厭了」(《 亞》頁 258 )
46 或許,這其中也夾雜著人道主義的關懷。我們再回顧太明擔任國小老師時 ,曾經隨日籍挍長到偏僻的龍眼村訪問。當時眼見生計困難的家長熱烈招待兩人 ,充當翻譯的太明心情自是沉重,但看不出是因為當買辦而內心不安(《亞》頁 57 )。 日後,太明見報紙誇耀一支日本刀砍了七十多人為英雄行為,徹夜無法 入眠(《亞》頁 197 )。 這時,再間接協助處死抗日分子,太明當然要良心不 安了
47 太明吶喊著:「依靠國家權勢貪圖一己榮華富貴的是無心漢!像食人野獸 ,瘋狂地鼓噪著,你的父親,你的丈夫,你的兄弟,你的孩子,都為了他,他們 為什麼高呼著國家、國家?藉國家的權力貪圖自己的慾望,是無恥之徒,是白日 土匪!殺人要償命的,可是那傢伙殺了那麼多的人,為什麼反要叫他英雄?混賬 !那是老虎!是豺狼!是野獸!你們知道嗎?」(《亞》頁 280-81 )
參考文獻
子敬。1969。〈由《亞細亞的孤兒》談吳濁流的精神〉《台灣文藝》 23 期, 頁 78
工藤好美。1974。〈評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灣文藝》45期, 頁3
古繼堂。1992年。《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
宋冬陽。 1985 年。〈朝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 收於陳永興編《台灣文學的過去與未來》頁 79-100。台北:台灣文藝
呂新昌。1995。《鐵血詩人吳濁流》台北:前衛
尾崎秀樹。1973。〈吳濁流的文學〉《台灣文藝》41期, 頁77-84
林柏燕。 1994 年。〈吳濁流的大陸經驗〉, 收於文訊雜誌社編《鄉土與文學─ 台灣地區域文學會議實錄》台北:文訊
林釗誠。1978。〈談胡太明的悲涼世界—試析《亞細亞的孤兒》〉《台灣文藝》 58期, 頁219-32
林浩。1984。 〈三讀《無花果》〉, 收於吳濁流《無花果》頁27-49。Irvine, Calif.:台灣
吳濁流。1971。《泥濘》台北:遠行
----。1977a。《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行
----。1977b。《功狗》台北:遠行
----。1977c。《波茨坦科長》台北:遠行
----。1977d。《南京雜感》台北:遠行
----。1977e。《黎明前的台灣》台北:遠行
----。1977f。《台灣文學與我》台北:遠行
----。1984。《無花果》Irvine, Calif.:台灣。
----。1987。《台灣連翹》Irvine, Calif.:台灣
----。1991。《吳濁流集》台北:前衛
陳映真。1977。〈試評《亞細亞的孤兒》〉, 收於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頁45-62。台北:遠行
陳嘉農。1987。〈為吳濁流《台灣連翹》出版而寫〉, 收於吳濁流《台灣連 翹》Irvine, Calif.:台灣出版社
彭瑞金。1978。〈吳濁流的殖民地文學〉《台灣文藝》58期, 頁177-90
----。1986。〈從《無花果》論吳濁流的孤兒意識〉《台灣文化》2卷, 頁15-19
----。1995。《台灣文學探索》台北︰前衛
張文智。1993。《當代文學的台灣意識》台北︰自立
張良澤。1975。〈吳濁流的社會意識—就其描寫台灣光復以前的小說探討之〉 《中外文學》3卷9期, 頁96-106 ; 3卷10期, 頁136-47
----。1984。〈《無花果》解析—從《無花果》看吳濁流的台灣人意識〉, 收 於吳濁流《無花果》頁1-26。Irvine, Calif.:台灣
黃娟。1993。《政治與文學之間》台北︰前衛
黃武忠。1980。《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台北︰時報
黃竹芳。1978。〈吳濁流小說論〉《台灣文藝》58期, 頁233-44
葉石濤。1966。〈台灣作家論(吳濁流、鍾肇政)〉《台灣文藝》12期, 頁25-36
----。1991。〈吳濁流論〉, 收於《吳濁流集》頁269-82。台北:前衛
鍾肇政。1967。〈《吳濁流選集》簡介〉《台灣文藝》14期, 頁43-44
----。1976。〈以殖民地文學眼光看吳濁流文學〉《台灣文藝》53期
----。1982。〈看!吳濁流文學〉《台灣文藝》77期
顏元叔。1973。〈台灣小說裏的日本經驗〉《中外文學》2卷2期, 頁106-21
瀧川勉。1974。〈殖民地統治下的台灣民眾群像—解說《吳濁流選集》第二卷〉 《台灣文藝》42期, 頁77-81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i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Aronowitz, Stanley. 1992.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Class, Culture,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Routledge.
Bhabha, Homi K. 1990. "Introduction: Narrating the Nation," in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pp. 1-7. London: Routledge.
Binder,Leonard, et al., 1971.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yle, Kevin. 1991. "Nothern Ireland: Allegiances and Identities," in Bernard Crick, ed. National Identitie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pp. 68-78. Oxford: Blackwell.
Chen, Edward I-Te. 1972. "Formosan Political Movement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914-193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pp. 477-97.
----. 1970.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Korea and Formosa: A Comparison of the Systems of Political Control."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pp. 126-58.
Connolly, William E. 1991. Identity\Difference: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raafsma, Tobi L. G. 1994.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on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in Harke A. Bosma, et al., eds.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pp. 41-61.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Graafsma, Tobi L. G., Harke A. Bosma, Harold D. Grotevenat, and David J. de Levita. 1994.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An Interdisciplinary View," in Harke A. Bosma, et al., eds.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pp. 159-74.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Grotevant, Harold D., Harke A. Bosma, David J. de Levita, and Tobi L. G. Graafsma. 1994. "Introduction," in Harke A. Bosma, et al., eds.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pp. 1-20.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Horton, John, and Andrea T. Baumeister, eds. 1996.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Isaacs, Harold R. 1975. Idols of the Tribe: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lapp, Orrin E. 1969. Collective Search for Identi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Kohn, Hans. 1944.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New York: Collier Book.
LaPalombara, Joseph. 1971. "Penetration: A Crisis of Governmental Management," in Leonard Binder, et al.,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p. 205-3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sker, Arnold. 1982. "A Question of Identity." Forum 44: Modern Jewish Philosophy, No. 44, pp. 59-67.
McCall, George J., and J. L. Simmons. 1978. Identities and Interactions: An Examination of Human Associations in Everyday Life. rev. ed. New York: Free Press.
McNamara, Dennis L. 1986. "Comparative Colonial Response: Korea and Taiwan." Korean Studies, Vol, 10, pp. 54-68.
Minogue, K. R. 1967. Nation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Murphy, John A. 1991. "Ireland: Identity and Relationships," in Bernard Crick, ed. National Identitie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pp. 79-89. Oxford: Blackwell.
Myers, Ramon H., and Mark R. Peattie, eds. 1984.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ubauer, John. 1994. "Problems of Identity in Modernist Fiction," in Harke A. Bosma, etal., eds.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pp. 123-34.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Serge, Dan V. 1980. A Crisis of Identity: Israel and Zio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fer, Boyd C. 1972. Faces of Nationalism: New Realities and Old Myth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Shih, Cheng-Feng. 1995. "The Emergence of Basque Nationalism in Spain: An Examination of Some Explanatory Variables."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No. 3, pp. 141-66.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83.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2nd ed. New York: Holmes & Meier.
Snyder, Louis L. 1976. Varieties of Nationalism: A Comparative Study. Hinsdale, Ill.: Dryden Press.
Tsurumi, E. Patricia. 1980. "Mental Captivity and Resistance: Lessons from Taiwanese Anti-Colonialism."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12, No. 2, pp. 2-13.
----. 1979. "Education and Assimilation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1895-1945."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3, No. 4, pp. 617-41.
Wheelis, Allen. 1958. The Quest for Identi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Zuckert, Catherine. 1995. "Why Political Scientists Want to Study Literatur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20, No. 2, pp. 18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