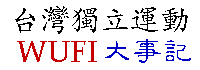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 與 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互動關係及經過
‥‥‥楊宗昌 口述 李錦容 編寫‥‥‥
美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主張言論自由和尊重基本人權。憲法保障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理想,且為自己的理想做出最大的努力來促其實現。但是想不到早期的台灣留學生,在美國為著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促成台灣的民主改革、幫助台灣成立為一個自由的國家,反而遭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的監聽、跟蹤和調查,造成在日常生活上許多壓力和困擾。那時期有很多兄弟姊妹們,先後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的調查和訪談。許多人都不便講出其經過和他們的故事,在此以楊宗昌記述於1970∼1984,14年間前後總共24次受到聯邦調查局情治單位人員調查和接觸的個人經驗。
美國聯邦調查局介入台獨聯盟在美國的活動
1960∼1970年代,美國政治單位和台灣的國民黨有一個合作計劃。這計劃就是由美國聯邦調查局供給國民黨在美國有台獨主張者的名單,由國民黨供給可能有傾向共產主義的中國人名單給聯邦調查局。
1970年,台獨聯盟由美國本部、日本本部、加拿大本部、歐洲本部和台灣本部五個本部合併成為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那時的主張與工作是群眾路線、總體戰和建國綱領。1970年,不但是世界性台獨聯盟的產生;同時當年三月彭明敏教授由日本台獨聯盟本部協助脫離台灣;四月二十四日鄭自才和黃文雄兩位同志勇敢刺殺蔣經國。因此美國聯邦調查局就對美國的台獨聯盟活動盟員相當有興趣。
報告資料的根據
這份美國聯邦調查局報告來源是根據兩方面的資料。其一是:根據美國國會於1966年通過一條“新聞自由法案”(The Freedom for Information Act)和1974年國會又通過一條“隱私權法案” (The Privacy Act)。頭一條是聯邦政府收集人民各方面的資料,同時人民也有權利知道政府所收集的資料;第二條是1974年,增加收集在美國有永久居留權的外國人的記錄。但是我在與聯邦調查局所接觸的前十年期間,並不知道聯邦政府尤其是聯邦調查局在做我的記錄。因此我直到1980年才拿到我的資料。
第二根據是:台獨聯盟是一個秘密組織,但是所有的工作都是公開的活動。在這組織訓練下,我個人養成一項能夠和聯邦調查局人員講很久的時間,且當他們離開後可坐下來把所有的談話做出完整詳細筆錄的能力。在此所採用資料有很多是我個人的筆錄。
那時代在美國有許多留學生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同志們不但是他們的家屬在台灣受到國民黨的干擾;自己在美國受到國民黨情治單位的種種不方便;另一方面又受到聯邦調查局做出許多干擾。
聯邦調查局的首次接觸
1970年七月,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首次來訪。那年的四月,黃文雄與鄭自才兩位同志為了要停止蔣經國特務頭子繼續屠殺台灣人,才勇敢採取剌殺蔣經國的行動。案發的三個月之後,因為黃文雄與鄭自才是由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保釋在外,所以聯邦調查局在支加哥的兩位資深工作人員James Foxe和John Mills來到我在郊外Brooksfield的住處。當時我剛好出去不在家,內人的妹妹阿基剛好在我家造訪,所以她開了門和那兩位工作人員談話。据他們的解釋並無什麼大代誌,因為楊宗昌先生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工作,他們只是要來了解他所從事的事務,問阿基是否知道黃文雄與鄭自才先生是否可能計劃要來支加哥看宗昌。阿基一無所知無法回答,所以他們就離開。
一個月後,1970年8月我們已經搬到Arlington Heights。有一日我下班回家時看到屋外停著一部車子,車內坐著兩個人,我心內猜想這可能是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果然不錯,不久就聽到有人按電鈴,開門後他們就拿出聯邦調查局的工作証給我看並要求進來坐。那時我無心理準備當然歡迎請他們進來做訪談。他們說蔡同榮教授是一位學者,在東岸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他們提醒我黃文雄與鄭自才雖然保釋在外但他們的行動是有受限制的,問我因為台獨聯盟的律師在支加哥,黃、鄭倆人是否會借著來找律師的機會向這裡的台灣人演講。我當然回答我完全不知道,且再進一步表示我也很想和他們見面,要求聯邦調查局若知道他們來的話煩請通知我一下。他們又繼續問我在支加哥地區台灣人活動的人名和這地區辦什麼活動。談了很久我完全沒把任何人的名字或活動資料給他們。那兩位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非常失望且說:「以後若有一天在支加哥地區出現一個黃文雄與鄭自才,他們的上司說他都不知道,這樣不會很困擾嗎?」我回答:「若我不知道的事怎能幫你們的忙。」他們也無法再說什麼,只好離開。
1970年代的台獨聯盟盟員沒有受到充分的訓練,我因為不知道自己應有的權利和義務,所以沒有拒絕聯邦調查局人員進來我家。這是第一次的接觸。
台獨聯盟處理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和我第一次接觸後的數年中,表面上好像已經不再和我接觸,但是實際上根據以後我所申請得到的資料,他們仍然繼續在暗中調查。1973年,我由台獨聯盟美國本部盟員大會選任為第一副主席,負責組織訓練部。我們感覺到有很多同志不了解如何應付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所以組訓部就編製訓練的教材,讓大家充分了解這裡的人民基本權利。因此我們與聯邦調查局接觸時才能依我們的權利有效地做出適當的應對。
1975年,我第二次當選美國本部的第一副主席。繼續負責組織訓練,所以在1975年,根據聯邦調查局內部資料,他們也已經查出我的一些資料,如在我居處所設立的組織信箱也包括在他們的調查記錄裡面。在我個人資料檔案中,包括是不是有暴力的傾向、個人資料、和在獨盟的領導階層。在這資料中並無寫出我確實是在負責些什麼任務。當然我的生日、身高、体重、頭髮及眼睛的顏色,住址、汽車等細節都例在記錄中。
從1970年後,聯邦調查局直至1975年才再度來和我接觸。那時來找我的是一位會講台灣話的John Sullian,另一位是會講北京語曾在台灣住過的Gary Andersen。這兩位的主要任務是在和我做第二階段的接觸。在這第二階段接觸中間,一年之內共來找我五次,主因是1975年7月23日蔣介石死亡後,美國感到有迫切了解台獨聯盟的需要,所以更加緊接觸。
國民黨從政治交換中所期待的利益
1975年將介石死後,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很積極的在台灣人中間到處找人。他們想知道我們在募款是不是要買軍伙,獨盟工作者所賺的錢是否都用在台獨運動上,台灣獨立之後在美國的台灣人是不是就是要回去台灣領導新的政權;若是蔣經國再來訪美國時台灣人是不是會再度謀殺他;或是若中華人民共和國邀請台獨聯盟的人去訪問時是不是會去。像這樣所有的種種問題,就無形中帶給大家產生一種大事臨頭的感覺,所以在1976年後他們曾經再度來找我很多次。
根據聯邦調查局檔案的資料,於1976年6月3日,蔣政權在美國的大使館接到一個沒有爆炸的炸彈郵包。五日後,聯邦調查局的書信中,有人報告住在支加哥的楊宗昌可能是此事件的嫌疑犯,所以就開始積極追查那炸彈郵包的來源,查詢到底從那裏寄的,誰做的?這就是1976年代蔣政權的駐外機構大使館、領事館,在台灣國內用其特務,在美國借用聯邦調查局的力量來再進一步的壓迫台獨聯盟運動者的手段。但是,對這炸彈郵包案件調查結果的記錄中都顯示與楊宗昌無關。他們承認在調查過程中,甚至於還提起這個被嫌疑的人可能是持槍戒很危險的人物。但是經過數月的追查、跟蹤、查案,他們的結論是那個情報不正確,當然這些調查都是在我自己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的。雖然蔣政權的國民黨在台灣用特務,在美國利用聯邦調查局企圖做進一步迫害這些台灣獨立運動者。但是,台灣獨立運動者都能夠運用自己的技巧和智慧去應付、對付國民黨和聯邦調查局。這就是聯邦調查局的人已經了解我在組織所扮演的角色之後和我的接觸。
聯邦調查局收集的資料與案件的連帶關係
聯邦調查局對個人收集資料時,因為他們都是在暗中進行,當然那位被調查的個人大多是完全不知情。為什麼聯邦調查局頭一次會找到我呢?這原因自然就會干涉到蔡同榮主席。蔡同榮於1969年7月當選美國本部主席,半年後於1970年1月,世界性的台獨聯盟成立時,蔡同榮擔任第一任主席,就在那一年,勇敢的黃文雄、鄭自才刺殺蔣經國。所以於1970年6月,當蔡同榮主席從紐約市他所住的家裡打電話到我支加哥的家裡時就被聯邦調查局接聽,從我所得的資料,顯示他們接觸我就是從那一通電話所導致而來的。在1976年10月,有王幸男郵包爆炸案發生,所以次年,1977年2月之後,聯邦調查局又開始忙著找尋人包括我在內。從聯邦調查局對我的檔案資料指出,他們感覺到調查局需要使用一個亞洲人的調查員,所以除了Andersen以外於1977年,他們又增加一位Jim Won。同年八月,我又第三次被美國本部選出為第一副主席,繼續承擔組織訓練的任務。聯邦調查局一直對我問詢有關謝東閔爆炸案的事情,無論他們怎樣問我還是不能給他們任何的回答,他們問不出什麼東西來所以在失望情況下才放棄和我接觸。此後至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兩年半中,聯邦調查局並沒有和我繼續來往,我好像是平安無事。
接觸過程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從1977年他們放棄和我接觸後,我就沒再受到聯邦調查局人員的干擾,這並不表示我真的可以開始過著平安無事的日子。1979年正月,美國和中國建交,於那年的12月10日,國民黨設計高雄事件陷害台灣菁英,五日後美國很快就於12月15日,由台灣人主張台灣獨立的團體成立台灣建國聯合陣線。這組織包括台灣獨立聯盟、獨立台灣會、台灣臨時政府、台灣協志會、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美麗島週報社、台灣民主運動歐洲同盟、潮流、台美公民協會與台灣人民自決運動等等台獨團體。他們的主張就是對國民黨政權立刻採取全面持續性不容情的攻擊,直到這個罪惡的政權澈底地從這整個地球上消失為止,這是一個很大的決心。
所以接下去在1980年後,在美國國民黨的辦公廳或是有關機構,尤其是中華航空公司,開始先後收到很多的武力爆炸威脅。親像王昇的兒子王步天在洛杉磯差點被炸死;高雄事件幫忙國民黨,王玉雲的小舅子李江林在洛杉磯被炸死。
種種代誌的發生帶至聯邦調查局於1980年2日又開始再次很忙碌,他們又開始和我接觸做出種種的訪問及拜訪。於5月23日,當時我是在支加哥一家工程顧問設計公司擔任經理,那天下午我的秘書用辦公廳的室內線電話告訴我有兩位男士要找我。我心內有數,因為之前聯邦調查局曾經找到我家,我就是不願意接見,現在有可能就是那兩位來了。所以我就對秘書講妳問他們是什麼人,叫什麼名字讓我知道。秘書很快就打電話回報,那兩位是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我就請秘書告訴他們:「沒事先約好時間楊經理不會客,請留下名片,回去辦公室後請給楊先生打電話約時間,他就會和你們見面。」
這兩位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就開始採取威脅的態度。問我們公司另一位經理:「你們有沒做聯邦政府的的工作?」這位經理回答:「當然了,我們是在做公路橋樑,這都是聯邦政府的工作。」他們就講:「我要見你們的楊經理為什麼他不接見。」那位經理就打電話問我為什麼不接見。我告訴他:「我們的工作非常忙碌,我不願意用上班時間和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談論與我們公司不相干的事。請轉告他們回去後打電話約時間,我會用下班的時間和他們談,只要首先約好絕無問題。」
他們離開後,我馬上打電話到支加哥聯邦調查局總部找他們的上司Mr. Superville。我問他:「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要去拜訪人時,是不是要事先約好才去?」他回答:「是呀!我們都是這樣的。」我立刻告訴他:「剛剛有您的兩位部下,其中一位是David Webber來要求見面,我工作非常忙,請告訴他沒有事先約好就來是很不禮貌的,叫他不應該這樣做。」然後就掛斷電話。
第二天,David Webber就打電話來:「楊先生,你怎麼那麼兇,害我被我的上司大罵一頓。」我告訴他:「對呀!是你自己的錯沒事先約好,又不是我不見你,若你先約好在下班時間我們就可以好好談,你沒這樣做是咎由自取。」聯邦調查局的人假裝不知道人民的權利,因為有很多人可能對聯邦調查局的人存有害怕心理,尤其是針對台灣在獨裁体制下來的人民。但是當時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大多數的人都已經接受到相當的訓練,了解人民的基本權利,所以對聯邦調查局的無理要求可以簡單應付。
處理聯邦調查局的干擾
1979年,美國台獨聯盟的代表大會第四次選我做第一副主席。從這一任開始我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此後四年中全力為美國本部到各地募款,因為當時聯盟的開銷相當大,得到很多募款經驗。
1980年5月底,David Webber正式打電話約見。我就給他我的律師的電話請他和律師連絡安排,約定6月3日下午一點在郊外律師事務所會見。那天,我十分鐘前到達我的律師事務所,等那兩位聯邦調查局人員的訪問。一點鐘整還不見人,律師打電話告知他們楊先生已在事務所等待不知你們人在那裏。David Webber回答律師說,約見地點定在郊外,聯邦調查局支加哥總部的上司不批準公家車子開出城,因為沒有車子所以不能來。我就請律師轉話:「今天楊先生誠心誠意準時來此等你們會見,你們既然失約不能來,以後免想要再和楊先生連絡,這是給你們最後一次的機會,是你們自己不守約,不應該每次都任意來打擾楊先生。」聯邦調查局人員答應律師,以後不會再打擾他的顧客楊先生。因為他們自己處理不適當,所以這時聯邦調查局要訪問我才會碰到困難,就此結束聯邦調查局支加哥總部的訪問。
對個人專業的影響
聯邦調查局十四年來調查中對我在專業上,以及美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長年來的政治活動是否有什麼影響,我願意以個人的經驗在此做一個說明。
1981年1月我就離開支加哥搬到加州的洛杉磯,主要是我用公開副主席的名譽在美國各地為台獨聯盟募款開發財源。所以我來到加州之後,聯邦調查局就減少和我接觸的機會。
我來加州所做的工作是與國防有關的工程設計,我擔任國家安全機密工程的工作,我就必須申請聯邦能源部國家安全調查。我來加州做這個工作的目的是,因為要澄清國民黨政權一直講台灣獨立聯盟分子是恐怖分子的扭曲謠言。主因是牽涉到1981年3月擔任加州司法部長的George Deukmejian ,曾經在1980年度報告中提起台灣極端分子是國際性犯罪的國際恐怖分子,然而國民黨就將Deukmejian講的台灣極端分子講成他是在指台灣獨立聯盟。為了要証明國民黨在這一字句上的扭曲,我就親身以我本人在台獨聯盟長期來負責公開的職位,向美國聯邦政府能源部安全國家申請安全調查,以此來定位台獨聯盟在美國司法部的定位。
1983年,我提出申請。在申請過程中調查了三年,最後到1986年才批準給我。這期間在1984年3月聯邦調查局人員來找我,他的名字叫Mark Mc Faddin他是關島來的少數民族,這次的造訪和我的申請並無關係,他說是要來保護我,我向他謝絕。但是於4月,有一天當我下班回家時看到外面有一部車停在那裏,我進門後不久他就來敲門要見我。他們告訴我得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派人來美國將對我有不利行動的情報,所以要來保護我。我告訴他們,我會保護自己,不願談此事,拒絕讓他們進門,並以事先沒有用電話和我約定時間的理由拒絕見面。這是聯邦調查局的人員來會見的最後一次。
我向美國聯邦政府能源部安全國家申請安全調查過程中,到最後的一關就是1986年,我需要到能源部接受安全官一小時的面談,在面談中提出很多我在聯邦調查局的記錄。最後安全官問我,楊先生你有什麼話要講,所以我就用十分鐘的時間說明台灣人在美國有很多優秀的教授、工程師和專業工作人員,但是其中有許多人就像我一樣都因為是主張台灣獨立的運動者,而受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陷害,又用不正確的報告來密告陷害,我們為爭取台灣的人權,結果我們本身失去最基本的人權。接著再告訴他,据我所了解美國是一個講道理有正義的國家,你是一位安全官,知道我在聯邦調查局的記錄全非事實,你現在應該去澄清我的清白,如此才是一個公正有正義的社會。
自從1983年我提出申請,經過三年的調查之後,終於1986年正式批準下來。批準的意思就是証明美國的司法部門知道,可以充分信任台灣獨立聯盟的負責人去做有關國家安全武器保護設計的工程,更進一層表示美國政府對台獨運動者有充分的信任。所以對我個人的專業來講,雖然是有些不方便但是在大体上來講,並不因為聯邦調查局的干擾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們在美國從事台灣獨立運動,長期以來有許多兄姊受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干擾,但是整個運動的進展,就是美國政府將台灣獨立聯盟當做一個政治主張、主張基本人權和建國運動的團体。所以今天我利用這機會讓大家了解在聯邦調查局的追查中,聯邦調查局也是不會輕易受國民黨的欺騙,他們知道什麼是事實、真正、有正義的人。進行欺騙的是國民黨情治單位的人,受害的當然是台灣獨立運動者,但是這些運動者因為他們有判斷能力、用智慧去克服在運動中所遇到的困難。以上是一個在美國聯邦調查局與台灣獨立運動互動關係的個案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