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族的歷史重建
![]()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I feel one of the obligations of the public elements of my intellectual life is to give voice to the dead, especially the victims….The living need history, too. Not to be made to feel guilty for a past they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or cannot change. The living need a history disturbing enough to change the present.Greg Dening (Neumann, 1998: 31)
The internalization of norms used in cultural discourse, the rules to follow when statements are made, the "history" that is made official as opposed to the history that is not: all these of course are ways to regulate public discussion in all societies.Edward W. Said 91993: 323)
臺灣自古不屬中國,我皇考神威遠屆,納入版圖。 中國滿清雍正皇帝(魏源,1997: 80)
若云番地,則全臺皆取之番,欲還不勝還也。藍鼎元 (1997: 61)
一、前言
台灣原為「原住民族 」(indigenous peoples) 世居之地,然而,四百多年來,由於來自中國(唐山)的漢語系經濟性、政治性移民相繼前來,在所謂的「開發」(settlement) 過程中,漢人挾其人口、以及生產上的優勢,使得原住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逐漸被邊陲化,不只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淪為弱勢族群,集體認同也遭到嚴重地侵蝕、切割;甚至於,由於受到外來統治者以夷制夷的手段荼毒,族人內部的自我歷史和解迭遭困頓,進而影響到原住民族的自覺,也阻礙到民族自決的實踐、以及自治運動的推進。
誠然,歷史的建構往往是具有選擇性的,也就是說,歷史的書寫會受到當代的思想傳統、以及當時的政治脈絡所左右。因此,我們所能看到的主流歷史,難免是經過搜尋而判斷是「可資使用的歷史」(usable history),甚至於呈現出由「外人」(outsiders) 對於「他者」(other) 所作的詮釋。這不是因為被支配者沒有自我描述、解釋、或是反思 (reflection) 的能力,也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意願,而是因為支配者的觀點代表的是政治正確,被支配者當然不會被允許作自我歷史敘述。
台灣的歷史一向由非原住民書寫(浦忠成,1999),在以漢人為「主體」(subject) 的前提下,原住民只是「客體」(object),看不到原住民族的觀點。特別是在傳統中國的五千年歷史建構中,不僅台灣的歷史被矮化為洪流中的淺溪,而作為中國「東番 」的台灣原住民族,更只不過是用來宣揚大漢天威的一個小註腳罷了 。
在近年所謂「本土化」的呼聲中,儘管「台灣四百年」逐漸挑戰「中國五千年」的史觀,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台灣既然被定位為「華人國家 」,台灣史當然是繼續以漢人開發的歷史為主軸。即使往日不經意流出的輕蔑已經掩飾,原住民仍然是聊備一格的「客觀環境 」,在導讀式的文字呈現下,原住民依然是歷史舞台上被動的行為者,甚至於是沒有面貌,彷彿要從這塊土地的歷史消逝無蹤。這當然是無法反映出幾百年來,原住民族為了生存所作的抗爭。
不管是武力消滅、還是文化同化,原住民族在歷史上的銷聲匿跡 (killing of history),代表的是集體認同的喪失 (killing of identity)。其實,「文化性滅種」(cultural genocide) 並不會比屠殺滅族來得仁慈?一旦失去獨特的認同,就沒有辦法確認民族的身分/資格,也就無法據之要求實踐民族自決權,連帶地,不僅被攫取的主權/土地權也將無法追討,而由自決權衍生而來的自治權原本是「天經地義」(inherent),也因此被迫要求「授與」(delegated) 。
對於歷史詮釋的認知,我們可以有三種模式 (modes)。從中性的角度來看,歷史關心的是「過去的未來」,也就是針對過去的記憶,為了未來在作競爭。如果從負面的角度來看,歷史只不過是支配者使用過去來合理化其霸權、或是暴力 的工具罷了。然而,從正面的角度來看,歷史建構是一種自我了解的方式,也是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以再現 (representation) 的進行來塑造集體認同。
儘管墾殖者的歷史再如何可歌可泣,片斷、切割的歷史畢竟不能代表所有住民的全貌,不能當作台灣民族要編纂的「民族史」(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如果「台灣民族主義」(Taiwanese nationalism) 的精神是包容的,企盼所有的住民願意共組一個現代的國家,那麼,每個族群的存在都是獨一無二的。即使人數只不過佔了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如果原住民選擇從國家「脫出」(extrication),不管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共和國」,漢人/華人國家存在的正當性仍然是不確定的。
二、歷史重建
原住民在漢字文獻上的最早出現,比較可靠的是清治時期文人騷客的旅遊記行 (travel narrative、travel literature),表現出的是浪漫的異國情調 ,彷彿是西方文明眼光中的「東方風情」(Orientalism),看不到具有歷史意義的原住民人物。這種Eric R. Wolf (1982) 所謂「沒有歷史的民族」(people without history) 的迷思,也被「原住民沒有﹝文字﹞歷史」所合理化。
從開發的角度/命題來看,冒險犯難的拓荒者為了保衛千辛萬苦而來的家園,必得面對懵眛兇殘的番人,因此,我們竭盡想像力所能抓住的,只是原住民出草的殘暴意象,宛如好萊塢拍攝西部片中的紅番。難道,除了戰士的角色以外,當年的原住民沒有像北美印地安人歡迎五月花號載來的白人一般,熱絡地接納來到新天地的漢人為鄰?難道,原住民未曾慷慷地傳授漢人求生之道 ?當漢人與原住民衝突的焦點,逐漸被轉移到人與大自然的競爭以後,原住民儼然被大自然所合併;在「人定勝天」的信念下,原住民淪為模糊的背景,在不知不覺中「隱形化 」而失去了歷史定位。
面對支配者視而不見的「歷史靜音」(silenced history),被支配者必須以自己的觀點來重寫歷史,奮力以「歷史存在」來擺脫他人的駕馭 (Adam, 1994)。Washburn (1987: 92) 指出,原住民族若要由過去的被剝削到未來的再起,端賴現在是否能在現在進行抗爭。又如Axtell (1981: 13-14) 所言,如果我們對於過去表示沉默,其實是對於那些作為的默許,那麼,未來歷史會再重演;他甚至於主張,學者應該有專業上的道德責任去打破「歷史孤寂」(Axtell, 1981: 13-14)。
在這樣的認識下,「歷史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並非單純對於過去的「再現」(representation) 而已,而是在關心我們如何想像嶄新的未來之際,為了要回應當前的需求,要不斷地去「重新建構」過去,也就是要去從事再詮釋 (reinterpretation)、再想像 (reconception)、再生 (reproduction)、重構 (reconstitution)、重估 (reassessment)、以及修正 (revision) 的工作。因此,歷史重建的目標不只是為了知識的取得(描述與解釋過去),而且是公義的實踐(消除支配、補償剝奪),更是要追求和平(避免未來衝突)(Wessner, 2001)。
面對歷史偏見,Belich (1989: 13-17) 主張除了以口述史來提供可能的另類描述外(到底真正發生了甚麼事情),更要想辦法去探究主流歷史體系是如何看待這件事(有怎樣的偏見),並且要嘗試去了解人們為何會有如此的詮釋(為何會有如此的發展)。也就是刻意地去選擇有爭議的事件 ,在我們被灌輸的傳統事實中去找尋疑點,進而根據可能的落差作歷史重建的場域 (Lorenz, 1999)。
在台灣歷史的重建中,原住民菁英雖然不滿以漢人為中心的開發史觀,卻彷彿認為歷史與其無關,因此,比較關注於民族誌 (ethnography) 的努力 ,也就是專心從事微觀的傳統藝術、語言、或是宗教的復育。Ortiz (1988: 9) 這樣說:「History is so distorted [that] it is irrelevant.」裡史扭曲大致可以解釋原住民對於包括非原住民的宏觀歷史論述的冷淡。其實,大多數原住民族運動者對於非原住民族群間的齟齬,一直是保持者冷眼旁觀的態度,以避免在政治上被迫選邊/靠邊站。
我們會同意,原住民族的歷史應該是由自己人來寫、以及為自己人而寫,也就是of, by, and for the Aboriginal Peoples。因此,原住民族為了確保自己獨特的史觀,歷史不僅不應該由他者所強加,也不應該受到外人所干擾。然而,除非殖民者、以及墾殖者尚未入侵之前的歷史,原住民的歷史若沒有對前者的描述,那就有如主流歷史對於原住民輕描淡寫般。如果說漢人心理想要忘掉先人開發過程,對於原住民土地的買、騙、偷、搶 ,也就是規避原罪般的歷史責任;相對地,原住民如果不願以原住民的身分參與公共領域的對話,除非是本身已經被成功地「白化」(whitened),選擇性失憶就特別另人匪夷所思。
因此,理想的原住民族歷史不是自我隔離的歷史,而是接觸的歷史 (Washburn, 1987: 92)。也就是說,在墾殖者的開發史以外,我們除了要有原住民族自己的生存史,更要有兩者之間如何互動的歷史。具體而言,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重建,除了證明自己的歷史存在外,還有三層意義:從原住民族與外來政權的關係,證明自己從來未曾放棄過自己的主權,因此,仍然保有土地權、以及自治權;其次,原住民族與墾殖者之間的歷史恩怨應該如何取得和解;再來,說明原住民內部雖然有分歧,特別是如何面對外來者的路線歧異,仍然有被征服的共同記憶,特別是平埔族雖然已被同化,族人過去的歷史經驗仍然有助於當前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未來定位。
三、原住民族與外來政權
葡萄牙人是在1544年「發現」福爾摩沙這個美麗之島,在此之前,原住民早在這裡自由自在地耕遊居住,與世無爭。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在17世紀分佔台灣南、北部分土地;西班牙人隨即為荷人所逐。中國明朝遺臣鄭成功在1662年驅逐荷人而建立王朝,開始大規模引入漢人進行土地開發。中國滿清王朝於1683年併吞台灣,因甲午戰敗,於1895年將台灣雙手奉上日本手中。二次大戰結束,台灣被盟軍交給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敗於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避秦來台灣,統治迄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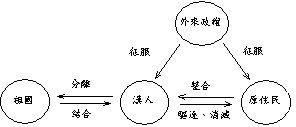
圖1:墾殖社會的政治架構
一般人習於將台灣定位為所謂的「墾殖國」(settlers' state),也就是由「墾殖者」(settler) 建立的國家;相較起來,一般的「移民」(immigrant) 多半只求「寄居社會」(host society) 的接受,而墾殖者則要在新天地有自己的國度,要切斷與「祖國」 (home country) 的政治從屬關係、以及文化臍帶關係而 (Hartz, 1971)。不過,台灣與諸如美國、加拿大、澳洲、或紐西蘭等墾殖國稍有不同,還要不時面對外來征服者入侵的威脅。
在這樣的架構下(圖1),台灣的土著的原住民族必須三面作戰 :同時要面對漢人移民、外來政權、以及虎視眈眈的漢人祖國。不管荷蘭、西班牙、明鄭、滿洲、日本、還是中國(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原住民族的眼光中,不是入侵的帝國主義者 (imperialist)、或是殖民政府 (colonialist government)、就是外來政權 (alien regime)。在殖民統治之下,原住民充其量是帝國主義在擴充版圖之際,必須加以征討 (conquest)、綏靖 (pacification)、治理 (rule) 的障礙。特別是從開發的眼光來看,原住民被墾殖者視為開發過程中威脅生命財產的「番害」,是需要處理的「問題」,「理蕃」成為重大的統治政策 。
當台灣被「納入版圖」之際,也就是台灣原住民族被剝奪一切的時候;雖說「台灣固土番之地」(連橫,1977: 329),然而,經過開山撫番,「其民既為我國之民,其地即為我國之地」(謝金鑾,1997: 93)。一般相信,征服的那一刻就代表原住民族的主權淪喪,因為只要征服者認為這塊土地沒有主人 (terra nullius) 、或是未加利用,一旦後續的墾殖者加以開發,就沒有所謂的所有權歸屬 (claims) 的問題。因此,不管當時的征服是否合理,只要強調墾殖者開發過程的堅苦卓絕,侵略的行止就可以加以合理化,也就是以血汗、或是生命來和上天換取土地所有權 (Curthoys, 1999);在這樣的思維架構下,原住民同意與否是不相干的。透過政策、以及法律的正當化,主流的歷史論述進行再生,不會有人記得原住民是如何失去民族權、主權、或是土地權。
根據歷史的記載,早期來自中國、或日本的海盜,已經有與原住民的短兵相交的經驗,甚至於特別是牡丹社事件。借用Michael Banton (1967) 的分類,這是一種「邊陲接觸」(peripheral contact) 的關係,也就是指兩者偶而有短暫的接觸,只在邊陲地帶作有限的財貨物交換、或是邂逅,並未真正的進行互動。
最早征服台灣的殖民者是荷蘭人,他們給西拉雅人帶來西方文明,包括宗教、以及文字;雖然彼此的定位不脫主僕關係,除了經濟支配外,還要配合軍事徵召,不過,平埔族至少有父權般的「照顧」來制衡漢人 。大體而言,我們可以用「制度性接觸」(institutional contact) 來描寫彼此的關係,也就是兩者雖然維持固定的接觸,然而,卻保有各自的中心結構,不因彼此的外圍作互動而有所變動;由於雙方並無資源上的競爭,這可以說是一種共生的關係 (Michael Banton, 1967)。
作為明朝旁支的鄭氏王朝,卻從未被墾殖者視為外來政權 ,恐怕是因為這是一個漢人政權;鄭成功驅逐紅毛番荷蘭人,台灣才能成為漢人的天下,此外,更何況由於他進行「反清復明」的大業,當然是漢人的民族英雄。一般同意,鄭氏王朝對於平埔族的壓迫,大致是嚴苛於荷蘭殖民者,可能是因為漢人政權不再需要非漢人幫忙監控。
在清治時期,政府顯然較為善待原住民,或曰,彼此皆非漢人之故;此時,原住民概被分為「熟番」及「生番」,分指有教化及未馴服的野蠻人。平埔原住民又有被驅策平亂(漢、番皆有)的價值 ,其中,巴則海族人甚至於被徵召渡海剿太平天國。不過,面對漢人蠶食鯨吞平埔族的土地,滿清政府無力制止經濟上的剝削,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漢化的滿洲政府似乎相信,文化上的同化 或可彌補原住民在經濟上的剝奪,不過,這種看來善意的接納,卻讓平埔族人失去認同以賴的原生基礎。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總督府的重心先是武力征服,繼而進行羈縻,在輔以實質的隔離。在「父權統治」(paternalism) 之下 ,殖民者為了討好「蕃人」來對抗漢人,分別稱之為「高砂族 」及「平埔族」,又多少有以居住地區為山區或平地之別。此時,平埔族人持續與漢化進行通婚 ,原住民的身分只剩下戶籍資料的登錄,只要自己不去提起,不會有外人去揭露;高砂族面對恩威並重的「撫育」政策,雖然逃過被漢人同化的命運,卻與漢人同樣被教育為皇民,興高采烈地參加太平洋戰爭。
戰後,內戰失敗而避秦來台的中華民國政府以漢人為主,對島上住民採取支配性的垂直統治 ,可以說是一個採取「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 (Hechter, 1975: 8-9) 的外來政權,也就是黃昭堂 (1998: 4) 所謂的「沒有母國的殖民王朝」。對於漢化(鶴佬化、或客家化)已深的平埔族,國民黨的基本態度是不信任,乾脆取消其在『中華民國憲法』下「少數民族」的原住民身分,也就是視之為本省人;更荒謬的是,平埔族竟然被歸類為與漢人壓迫者同類。對於人數稀少的所謂「山地同胞」,國民黨大致以分潤的方式來收買菁英,同時要防止各族的團結。
自從由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到陳水扁的「台灣中華民國」,逐漸本土化的中華民國政府是否仍為外來政權?在漢人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 想像中,四大族群(原住民、外省人、客家人、以及鶴佬人)的建構方式當然不敢排除原住民(施正鋒,1999),因為原住民畢竟是亙古以來「真正」的「本地人」。長期以來,面對漢人社會的蠶食鯨吞,原住民不只是被支配的弱勢者,更是被外來移入的墾殖者所殖民者;站在原住民的立場,由被軍事征服、土地剝奪、政治支配、到經濟剝削,任何以漢人為中心的政權都會被視為外來者。
四、原住民族與墾殖者的和解
墾殖社會算是一種特殊的殖民地,也就是殖民政權一旦與母體脫離/爭霸(鄭氏王朝、國民黨政權) ,它就必須認命留在殖民地而「無法離去」,除非是被對方(滿清、中華人民共和國)吞噬;相對地,墾殖者的後代則「不想回去 」,因為他們想要有自己的國家。不管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共和國」,漢人墾殖者的後裔仍然要面對原住民被征服、剝奪、以及支配的事實;新移民雖然並未參與當年墾殖過程的剝奪,卻同樣享受開發所帶來的成果,也就是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上的支配,自然不能因此置身於外,彷彿這只是舊移民與原住民的事。
表面上看來,漢番之別「只不過」代表著分類上的方便,用來區別文明與原始的差異「而已」,事實上卻反映著強烈的「種族主義」(racism) 的色彩,也就是以天生的體質優劣決定一群人命運。對於大多自認為是漢人後裔的本省人來說,原住民只不過是相對於「平地人」的「山地人」;太平洋戰爭、以及二二八事件中曇花一現的結盟 ,並不能改變漢人自我中心對「番仔」的輕蔑。
對於原住民來說,所有的漢人原本都是「白浪」(歹人),特別是面對本省人的視若無睹,國民黨的恩寵來得實惠多了;當然,現代墾殖者持續採取的資本主義式土地侵蝕,也讓原住民菁英憂心忡忡。隨著國民黨政權而來的政治性難民被稱為「外省人」,其中,單身的「國軍」以經濟優勢與原住民通婚,讓原住民文化有打入主流媒體的空間;不過,第二代的認同卻是模稜兩可,而原住民身分的開放又與土地經濟糾纏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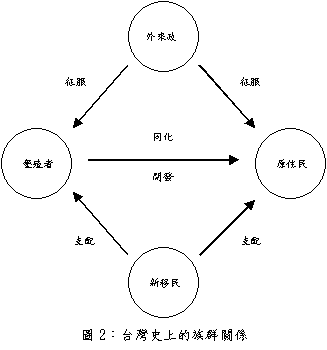
我們可以看出來,國民黨政權絕對不願意本省人與原住民結合,譬如在二二八事件中短暫出現對抗外來政權的聯合陣線。因此,當本省人以本土住民的身分喊出「乞丐趕廟公」、期待「台灣人出頭天」之際,原住民便被慫恿出來挑戰,以「誰是真正的台灣人」來否定本省人自決的正當性。原住民立委林天生在質詢時表示:「台灣山胞才是台灣人」(馬起華, c. 1988: 45)。王育德 (1999: 28) 認為這種說法「企圖使台灣人覺得自己也是侵占者,產生虧欠心理」。這樣的經驗,或可解釋本省人政治菁英多對於原住民議題的意態闌珊。
隨著墾殖/移民社會的逐漸「土著化」(indigenization),土生土長的漢人(本省人)對於外來政權的漸生不滿,便有所謂的「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一直到近年來方興未艾的「本土化」(naturalization) 運動,可以視為對外來佔領政權的抵制。然而,到底本土化的內涵是甚麼 ?原住民族的角色如何?既然回歸本土成為由壓制中尋求解放的不二法門,那麼,唯有恢復固有的純樸文化,長期被禁錮的靈魂才能獲得救贖。如果說漢人要回到中國去尋找源頭是荒謬的 ,勢必要由原住民的文化去搜尋滋潤的母土。
然而,對於大部分的漢人來說,台灣是一個「華人國家」 (Chinese state),是由土生土長的漢人想要建立的國度。這樣的論述當然是折衷式的作法,在企圖切斷與中國的政治臍帶之際,卻又想要保存華人文化的特色;因此,本土化代表的是「土生仔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 式的(Anderson, 1991)。在這裡,「台灣人」想要「當家做主」的訴求,代表的是本土菁英對於外省族群長期支配的不滿,特別是在國民黨體制內上升 (upward mobility) 受阻者。我們看到的,其實是一群被漢化的平埔族「混血兒」(mestizo ),費勁地在扮演土生仔(creole)純種漢人,以想像中的文化優越感來鄙夷原住民(黃昭堂,1998:160)。
既然「漢即番」、而且「非漢即番」,因此,「番即非人」。只要華夷之辨的種族藩籬仍然屹立不搖,漢人想像中的優越性依然揮之不去,那麼,原住民注定淪為要被同化的對象。因此,本土化當然不會是尋求「原住民化」(indigenization),而本土文化也看不出會允許呈現看似南洋風味般的原住民文化。不管是本土化、還是含混的「台灣優先」,與中國國民黨政權的「中華民族」(Chinese Nation) 論述相較,彼此在形式上的差別不過是心靈歸屬的中心為台灣、還是中國,土生仔漢人民族運動的訴求就顯得空洞。對於原住民族來說,不管是改朝換代、還是政黨輪替,只不是換了一個新的統治者;終極而言,台灣只不過是漢人倔強地要移植的「新中原」。
相對地,如果我們不排除漢人墾殖者的後代為「本地人」(native) 的情況下,可以把台灣的政治發展過程,看為是如何將一個傳統的漢人墾殖社會,脫胎換骨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嚐試。在這樣的了解下,原住民族、漢人墾殖者、以及新移民都相同的機會參與「國家的締造」 (state-making)、「民族的塑造」(nation-building)、以及「政治制度的建構」(state-building),那麼,大家都是塑造中的「台灣民族」(Taiwanese Nation) 的成員,而且個人的權利、以及集體的地位相等,如此建構的國家才不算外來政權。
五、內部的整合與平埔族的定位
當滅族為道德上所不許可、而驅逐出境不可行之下,如何吸納、收編原住民成為統治者的要務,特別是在面對原住民的軍事、政治、或是文化抗爭之際,外來力量可以操弄部落(族群)間原本的衝突,這不僅會破壞原住民內部的政治生態平衡,崩解泛原住民運動的團結,也左右原住民與外來者的關係如何定位。
從征服到納入,雖然是以衝突為主要的互動模式,也有攜手合作的現象。面對外來力量壓境,原住民可以選擇的路線不外合作、或是抗爭 (Belich, 1989: 29-30)。究竟是和是戰的背後,可以代表原住民菁英對於倚賴性的接納、或是排拒;也可以解釋為對於外力的工具性考量,也就是在允許墾殖者的勢力擴張之下,是否會因為外來的奧援而鞏固自己的力量,或是因為遭受外面強烈的壓力,反而因為同仇敵愾而達到內部整合;至於各族對於泛原住民運動的整合表現出冷淡、或是配合的程度,也可以詮釋為對不同位階的集體認同的接受 (Dowd, 1992: xxi, 20-21, 30)。
戰後,日治時代的「霧社事件」在能獲得國民黨政權的褒揚,主要是莫那•魯道的抗日行為合乎中國人反日的政治教條;另一方面,由於當時族人刻意不殺漢人,也被本土意識較強的觀點解釋為彼此已發展出有同胞愛。然而,族人內部迄今對於莫那•魯道的歷史定位,仍然有南轅北轍的評價。也就是在高度抽象的「捍衛主權」論述、或是抗拒差別待遇的結構性解釋之外,部落間的路線之爭仍然要決定於領導者對於族人/同胞/自己人的定義。
在四百年來的開發史中,如果說原住民被邊陲化的話,其中的平埔族(熟番、化番)則在漢化的過程中被虛無化。在清治時代,位於漢人以及高山族夾縫中的平埔族人,在土地逐漸流失的過程,不免有人因為經誘因而自願充當隘勇,既守又攻(柯志明,2001;Shepherd, 1995):從漢人的眼光來看,這些歸化的番人比較值得信賴;然而,站在原住民的立場,這些平埔族兄弟卻是叛徒。迄今,這種「既漢又番」、「非漢非番」的尷尬歷史角色仍然有待和解。
其實,平埔族最難抗拒的還是文化性的暴力,因為漢番之別不是單純的血緣、或文化上的分類,或是族群認同的差異,而是強制就文明教化作優劣等級的排序,因此,他們必須選擇接受同化、或是保存文化差異而飽受歧視。漢化是一種社會逃避,的平埔族用來排拒漢人硬加的種族主義式枷鎖;平埔族希冀透過血緣上的融合 、以及文化上的同化,來取得漢人的認同 (Brown, 2000)。唯有小心翼翼隱藏自己的認同,將自己的價值、態度、以及行為向漢人看齊,才能獲得集體的自我救贖;平埔族唯有不斷地進行漢化來提昇個人,才能防止自己「重返野性」。不管是被動、還是積極尋求「作人」(當人),水乳交融式的境界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假象。
目前,盛行的說法是墾殖者的後代都有平埔族的血統,並且運用科學的方式來證明民間流傳已久「有唐山公、無唐山母」的的說法。其實,不管後裔是否願意承認,歷史早有明證,隻身前來台灣探險的男性漢人(羅漢腳)大量與平埔族女性通婚;然而,認同畢竟是主觀的自我認知,而客觀上的血緣相近並不保證認同就會親近。坦承而言,經過「白化」(漢化)的這些混血兒,即使政府同意開放身分的回復,令人懷疑有幾成願意確認自己有「番仔」(原住民)的污名。
進一步來看,即使大部分的「平地人」終於決定接受母系的平埔認同,實質上的意義又是如何?也就是說,平埔族的原住民身分的政治影響為何?在彼此的關係尚未取得定位之前,我們當然認識到,平埔族與高山族原本都屬於南島人 (Polynesian-Malayo、或Australoid)。然而,由於居住地的分布不同,遭受外來侵犯的時間有先後之別,特別是日治時代的隔離措施,暫時遲緩漢人開發的侵蝕。或許有不少真正的平埔族人企盼歸樸返真,想要捍衛文化上、及血緣上的純真,也就是要取得身為原住民的榮耀。那麼,除了原住民的身份,平埔族的後代要如何來與高山族作共同想像?
原住民(高山族)又如何看待平埔族?除了願意接納與他族通婚者的子女外,原運的菁英大致傾向於分享原住民身分予平埔族(尤哈尼•依斯卡夫特特,1997),而新政府的原住民事務決策者多原運出身,對於平埔族的體制內地位已表達樂觀其成的態度,也就是如果能根據日治時代的戶口資料証明自己是「熟番」者,將可回復原住民身分。這代表的是作為「生番」後裔的原住民對於族群認同的局部開放,而非對所有帶有平埔血統的漢人張臂擁抱;除了如何分配有限資源的考量外,最重要的恐怕是擔心絕無僅有的「原住民性」(indigenousness) 也會被漢人攫取而去,也就是懷疑他們在主觀上有多少原住民意識。
六、結語
站在多元文化主義的角度,對於台灣這個多元族群、多元民族、甚至於多元種族的國家來說,不管人數的多寡,每一個組成份子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有至高無上的貢獻,也因此,我們有義務將原住民族豐富的歷史資產呈現給大家。儘管政權轉移,整個社會依然被舊日的單一文化思維所支配,「華人國家」的自我定位仍然是台灣當前的論述主流;這不只罔顧台灣是多元族群的事實,更對於原住民族的存在視若無睹。在《台灣論》(小林善紀,2001)出現以後,讓我們深深驚覺到,如果大家對原住民族的歷史完全沒有起碼的認識,根本是談不上相互尊重、欣賞。如果彼此能透過當前的對話,對過去的歷史取得和解,才有可能對原住民族未來的自治獲得共識。
如果我們真的要進行「歷史和解」(historical reconciliation),必須要先能勇敢而老實地挑戰過去,也就是承認先人墾殖的背後隱藏的是殖民的本質,然後心甘情願接受原住民被剝奪的全盤責任/原罪,再來是誠心誠意進行補償,並且能協商建構彼此相需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架構,如此一來,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間的共同想像才有意義 (Neumann, 1998; Green, 1995)。
然而,只要原、漢之間不能進行真正的對話,不能協商民族對民族的條約,則國家存在的正當性就永遠不能確立。其實,問題不只是在政府不承認原住民的民族權利,癥結更在漢人不願將原住民族當作對等的夥伴來看待。漢人若是持續拒絕與原住民進行和解,則漢人內部自己三個族群的分歧又如何能化解?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齟齬,又豈有可能調解?
不管是平埔族、還是百越族的論述,兩個方興未艾的途徑試圖以血緣上的mestizo(混血兒)來跳開漢人血統、以及華人文化的陷阱,費心地排拒「中國人」黑洞的吞噬,卻又捨不得放棄文化上的優越感,在睥睨中,彷彿已經無法欣然接受原住民的純樸文化。誠如黃昭堂 (1998: 81) 在評論廖文毅的「混血論」時所言,這是要區隔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或中國民族最便捷的方式。然而,面對各種「去漢人」的努力,台灣人內涵的建構必須有超越百越族/平埔族的論述,如此一來,「非百越族」(外省人)、以及「非平埔族」(原住民)才有參與民族想像的空間。
除了原生式的血緣描繪,民族認同的靈魂還可以使用其他三種方式來建構。「台灣住民」指的是只要在台灣出生,就可以取得住民的身分,強調對土地的愛;「台灣國民」強調對國家的效忠;「台灣民族」則堅持以共同體的實踐來凝聚多元族群。土地只不過是國家的成分之一,重要性在人民之下,本身並無超越人以外的真正價值;同樣地,國家是體現民族的最高政治型式,只有在結合民族之下成立民族國家,國家才有存在的意義,否則,將只是某個族群/階層用來控制他人的工具。包容性極大化的「多元文化」應該是優於虛矯的「融合」、或是排他性的「同化」。
那麼,作為歷史「主體」的原住民,在何種條件之下,願意被漢人國家「吸納」(incorporate)?也就是說,原住民的「民族」(peoples) 究竟要如何與漢人的「民族」(nation) 來接觸(或接軌)?我們或可將台灣定位為由兩個對等民族共同組成的國家,而非「民族中的民族」。這當然不是單一的政治體制 (unitary),也不是地域式的聯邦 (federation),卻比邦聯 (confederation) 的安排更強,我們姑且稱為「特殊的民族與民族關係」。在這樣的架構下,原住民並不是放棄獨立建國的選項,而是同意有條件地行使自決權,並讓渡一些原住民主權,以交換漢人對土地權、以及自治權的讓步 (Kymlicka, 1998)。至於漢人是否願意承認原住民的這些集體權利?那要決定於原住民與漢人國家的「夥伴關係」如何定義。